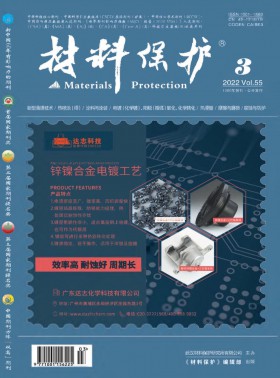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灯戏的保护与传承,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下,在川剧引领的四川地方戏曲剧种的展演活动中,灯戏这一主要活跃于我国西南的地方小戏,从荒村僻壤走近都市大众的视野,步入现代演艺的社会空间。2010年10月,在“中国•南充嘉陵江灯戏艺术节”举行的灯戏专场展演活动及灯戏论坛上,拙朴风趣的灯戏表演不仅开拓了其展演的文化空间,而且引发了与会学者关于灯戏剧种特质和属性的更多关注和讨论。在多元文化力量不断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灯戏如何保存本剧种自身的独立品格和主体性,如何在原生态、展演态和衍生态不断转换的文化语境下,释放出内在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力量。我以为,重新考量灯戏的功能定位,反思灯戏的生态构造,无疑是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 一、灯戏的功能定位:娱乐性与实用功利性 灯戏是流行于我国川、渝、云、贵等西南多个省市的民间小戏,在过去,多与春节、灯节、庆坛等民俗、祭事活动结合在一起。川北灯戏流行于阆中、南部、仪陇、顺庆等四川东北部地区,剧目题材多反映川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现有剧本200余个;唱腔来源于民间小调、神歌、佛歌、嫁歌、端公调等,分正调和花调两类;表演以丑、跩、笑为特征,融会了木偶、皮影、猴戏、民间歌舞等多种技艺,诙谐风趣,被农民称之为“喜乐神”。川北灯戏作为民间小戏,以二三旦、丑角色的斗嘴、打趣,以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将饱含地域风情和民俗事相的笑谑故事连缀起来,以拙朴、轻松、欢快的气氛供人消闲、娱乐。川北灯戏在表现重大题材和挖掘严肃主题上,不是它的特长,也很少涉及关于生命与人性的文化深耕。但此次观摩的川北灯戏剧目,却引起我不一样的思考,如何理解灯戏的娱乐性和实用功利性,或者说,在娱乐与实用背后,灯戏还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此次灯戏展演聚合了川、渝、滇、黔等地的灯戏表演团队的精彩剧目,川北灯戏的表演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灯戏艺术节从展演活动开幕式起就拟造了一场民间灯节的狂欢,而每场都有的“开门灯”,更以热闹、欢快的场景,渲染出一种喜乐的氛围。川北灯戏《送灶神》的轻俏热闹、《灵牌迷》的诙谐风趣、《打判官》的荒诞怪谲,欢快的形式、娱乐的表象体现了灯戏的内在精神和特质。《灵牌迷》将馋懒成性的小俩口终日游手好闲、混吃骗喝的行径表演得惟妙惟肖。然而此剧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却不仅于此,为了乞讨骗钱的伎俩不被揭穿,一番谁先死谁后死,在一场怎样装死的争论后,小俩口设计在家中设灵牌装死,愚弄慈善的老者。窥见真相的两位老人将计就计,以装殓裹尸逼小俩口“起死回生”,最终一卷白布裹住的是小俩口好逸恶劳的手脚。《送灶神》则将日子拮据的山野小夫妻祈拜灶神庇佑赐福的生活愿望表现得情真意切。看似拙朴的小媳妇却充满风韵,引得灶神也频频下凡垂顾,一场献鸡祭灶的虔诚,演变为打情骂俏、鸡飞狗跳、活色生香的人神对手戏。灶神在小媳妇含情双目、娇嗔身姿的引逗下,不禁向人间大倒苦水:原来小灶神在天庭等而下之,自己尚且衣食不周,哪里承托得起人间百姓的仰仗。真是神仙比俗人还烦恼,寂寞天上哪比自在人间。在先出场的灶神和后出场的丈夫之间,在笑骂、调情的游戏场景与严肃、虔诚的祭拜仪式之间,村妇和灶王爷周旋在一个颇有意味的张力场中,且不说小媳妇为博得灶神的青睐,有意羞涩扭捏和媚眼煽情;更有意味的是丑扮的灶神爷人间天上的颠倒臆想:有漂亮小媳妇可以娱情,有美味鸡筵可以享用,有受祭赢得的尊荣和敬重,有行走在地的踏实和自由,贫贱夫妻竟成了灶神羡慕的一对福人,恋恋红尘也成了灶神眷顾的一片乐土。《打判官》借地狱为人间说法,将贪官死了以后在阴间才能讲出来的故事,变成了活地狱最好的注脚。形销骨立、琐碎而短视的判官,风骚丑陋、悍妒而多情的夫人,碰上了生死路上要钱不要命,到了地府仍贪性不改的贪官,演绎了一段荒诞的阴阳判。人间物欲的赤裸贪婪,与地狱判官的家事风情,形成了滑稽的映照与颠倒错置。一份生死簿的勾划,一场活地狱的审判,绘刻了人性的阴暗、堕落造成的灵魂变态与世风扭曲。 或许有人会说,川北灯戏的表演着意的是“打”、“闹”、“笑”、“俏”,场面虽好看,主题表达却过于混杂;笑料虽不少但剧情构造却全无章法。比如《嫁妈》编排的是一对母子的憨嗲,《灵牌迷》絮叨的则是一双好吃懒做的小夫妻,《闹隍会》炫耀的是县老爷的竿技,《送灶神》拉扯的则是村妇和下凡的灶王爷弄风情,《包公照镜子》演绎的是硬汉子的心里软,但镜子却把故事说走了,《打判官》原本是打贪官的,却成了酒色才气的混搭。川北灯戏是民间小戏,毋需向大剧种的剧情统一性、结构完整性看齐,这些看上去的任意装点、轻浅亵玩、无伤大雅的卖弄风情,使得故事情节随意转换,说口东拉西扯,“喜乐神”的表演风格,把一切神圣的仪、礼都做了世俗化的处理,抹去庄严、亵渎权威,甚至跳脱剧情与观众直接对话,极尽狂欢与笑谑。在娱乐的表象下,最戏谑的质料包纳了最残酷的元素,最光亮的空间洞穿了最黑暗的一隅;玩世不恭的面具保存了小人物活着的尊严,调侃生死的游戏解构了天上人间的秩序。这些剧目非常突出而一致表达的是强调世俗女性在生活中的主动性,思忖自嫁的妈妈尽力想改变贫苦无依的生活,馋嘴的小媳妇用刁蛮的手段折腾懒睡的丈夫,判官夫人不但以凶悍唬倒当家的,还拿风月娇宠自己的小丈夫,祭灶的村妇更是把天神逗弄得脚不点地、神魂颠倒。在旧时代生活氛围中,原本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女性,川北灯戏则以性格的绝对强势和“亦正亦邪”的风情,不断争取着自己应得的生活权利和人生幸福。正是这种性别错置产生的生存幽默感,演绎了蜀文化独有的情韵,伸张了小民重实用的人生态度和在劣境中立命求生的意志。川北灯戏借人神共论生死、人鬼轮回转换,传达出颠倒世相、举重若轻的另一种底层生活的真实,这就是笑对苦难的无畏、解构生命庄重的谐趣、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快感混合而成的民间笑谑精神的力量。 此外,就现存川北灯戏的剧目看,有一部分是“天上三十二戏”、“地下三十二戏”①这样一些与端公、庆坛仪式相关的故事,但这些与民间祭祀仪式相关的搬演形式在向现代社会流传的过程中,却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被剔除了。从此次演出的川北灯戏形态上看,虽然不少剧目涉及了神灵的角色,但除了每场演出的“开门灯”以及跑龙套的灯官,还能让人联想到与端公、庆坛相关的一点遗存外,川北灯戏表演中与民间祭祀仪式相关的程式、仪式,以及附在这些程式中的祭祀活动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川北灯戏传承与保护中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在重视其现代语境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它对于百姓生活和底层社会的精神抚慰功能,这种酬神、娱人的实用功利性是川北灯戏在民间社会得以生存的无法剥离的重要根基。#p#分页标题#e# 二、灯戏的民间生态:非遗的主体及文化空间 灯戏展演作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一项活动,聚合了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传媒、传承人群体及普通观众等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参与。其中,政府是非遗工程的主导者,企业是项目效益的促动者,学术研究机构与传媒是其文化价值的评估者和社会影响的传播者,而作为非遗主体的传承人和普通观众,在这一系统中似乎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传承人的演艺活动要仰仗官方的政策主导和财力支持,要依赖企业的市场运作和商业盈利,还要借重学者评点和媒体传扬,而普通观众在剧院观摩和广场展演中的整体地位和互动作用,似乎被边缘化了,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非遗的主体究竟是谁?灯戏的文化空间在哪里? 展演为我们提供的审视模本和表演形式其实是非常态的,是自上而下的,它是灯戏文化空间的一种再生和延展。这种再生和延展,如何融入、贯通民间自发的、原生的灯戏表演生态?民间自发的原生乡班、草台灯戏演出形态,其实更能代表其生存所必须依赖的特定文化场域和空间。灯戏的演出形态,更需要保护的是传承人与观众组成的共同体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空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灯戏不是表演和观赏,更是他们亲历、参与、实践着的一种生存方式。而目前的状况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帜下,作为展演、观摩的灯戏表演生态受到更多关注,并明显获得改善,而民间自发的、原生的、家班的、草台的灯戏表演生态却出现了停滞、衰退。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在原生态与展演态之间,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在乡民社会与现代都市之间,灯戏的表演生态其实存在着一些真空与断裂地带。 如何加强灯戏传承人群体及其文化空间的多样性、整体性保护?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活动,如何转化为灯戏传承人的群体文化认同和自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并在商业利益下保持遗产主体的独立性,而不被利益追逐所异化、拆解,这是灯戏保护实践活动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而此次展演的川北灯戏代表性剧目,可以说展开了这种多样性、整体性保护的探索和尝试。如《裁衣》的故事,只有放在龚裁缝的老式熨斗和王大妈的“粪水”里,才有了绝妙的韵味。龚裁缝那套“老掉牙”的裁缝技艺,王大娘那些琐碎的家长里短,还原了蜀地人文的历史记忆,也激活了人们对逝去生活光景的兴趣。《闹隍会》舍弃了威官加恩,垂怜小民的套路,将传统的清官题材加以变形。与城隍同庚的县太爷因为生日清冷,乔装扮城隍,微服察民情,一路上坐轿玩竿、渡河涉险,将一个波澜不惊,没有多少剑拔弩张的官民矛盾演来跌宕起伏,充满风趣。在巧设计囊、调弄城隍的小民大智慧激励下,一个注重实务、亲民爱民的清官形象跃然场上,而乡里隍会的热闹亦铺染到了都市剧场观众的眼前上。《包公照镜子》摆脱了黑脸包公清廉办案的故事框架,放大了包公和小孙女促膝攀肩、亲和蔼然的家庭游戏场景。铡美后归家的包公,因卷入皇族纷争和权力角逐,思前想后,内心焦灼。照镜子的“变脸”,反射出皇后的跋扈、秦香莲的悲苦,通过日常家庭生活细节表露了包公心灵深处的矛盾苦闷:因主持正义、秉公执法不但使自己陷入权力网罗,还牵连秦香莲陷入遭受非议的窘境,加上王朝、马汉的“众叛亲离”,使包公对自己的抉择也产生了一时的动摇和怀疑。地域文化镜像对包公戏段落细节的舍与取,再现、还原了包公人性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可以看出,通过传承人群体的努力,这些川北灯戏的展演剧目传递了弥合断裂、保护灯戏生态多样性的信息。 此外,灯戏论坛的专辑资料《四川灯戏集》,让我们在有限的看戏之外,触摸到了更丰富的川北灯戏遗产。例如,其所选剧目《补缸》,又名《锯大缸》《大锯缸》《大补缸》《王家庄》《百草山》《百鸟朝凤》等,原本出于明代传奇《钵中莲》。原剧写百草山上的旱魃化身王家庄王大娘,取死人噎食罐炼成黄磁缸,用以抵御雷劫,但缸为巨灵神撞裂,王大娘觅人补缸。观音遣土地幻化为补锅匠人打碎其缸,旱魃与土地展开神妖大战,最后观音请天兵斩除旱魃。在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中都有的这部神话剧,在《四川灯戏集》里,却完全摒弃了神妖大战的荒诞离奇和惩恶扬善的教化主题,甚至也删除了其他地方戏所刻意渲染的武打、走跷和变脸绝技,开篇即展开了王大娘和小炉匠因补缸而讨价还价、调情斗嘴的喜剧性情节,不但小炉匠由土地变化、砸缸除害的意图化为乌有,且在南方流传的故事中小炉匠踩王大娘绣鞋的细节,在灯戏里也被改为扬沙迷眼、伺机逃跑的更富有蜀人黠趣的举动。还有意思的是,王大娘在缸被打裂后也没有流露出任何难过的沉重心情,更没有伺机报复的起意,反而即刻转念、生火做饭、打点衣食,这些举动,完全表现的是蜀地老妇和游贩匠人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插曲。在《四川灯戏集》收录的其他剧目中,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韩湘子度妻》《雪梅教子》《小放牛》等,都或多或少与其它地方戏截取的故事段落和着眼点不大一样。为什么截取的是“这一段”,而不是“另一段”,四川灯戏截取的故事和表演故事的着眼点和趣味性说明了什么?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原生态,是植根于蜀地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中的原生态。应该说,原生态并不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低级、粗糙的原始状态,原生态更不是贫困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原生态体现出的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聚落性,也表达着遗产传承人的主体性和自觉的文化选择。所以,灯戏的保护除了表演技艺的保护,还应该包含灯戏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文化传统多样性的保护,包含传承人及其一方受众共同享有的文化权利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强调的是文化活动与文化空间的互相依存,而非单一的文化样式;强调的是活的整体,是与一方百姓的生活、信仰、精神追求密不可分的特定生存境遇与文化样态。灯戏的保护无可置疑地需要面对整体性保护、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如果我们能通过南充灯戏的展演及论坛活动,重新思考灯戏的功能定位和民间生态构造问题,更多地关注作为遗产主体的灯戏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诉求,进一步探究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聚落性,自觉地促成传承人的身份归属和遗产地的文化认同,那么,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融入由原生态、展演态和衍生态联结起来的社群文化共同体和大众文化场域,才能使川北灯戏的保护血肉丰满并不断生息,充满鲜活的生命力。#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