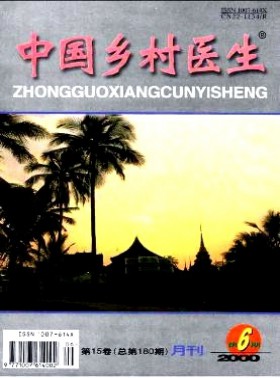【摘要】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具有云南元素、儿童元素、新媒体元素等特点。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是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三个典型文化体现。儿童电影作为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分支,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不仅传播了云南的地域文化,而且也传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关键词】儿童电影;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
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具有云南元素、儿童元素、新媒体元素等特点。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电影数量不少,多部电影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儿童电影作为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分支,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不仅传播了云南的地域文化,而且也传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一、童年情结
童年情结又可称之为童年体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感情、知识、意志等[1]。童年情结是一个人成长的力量源泉,是生命记忆力量的源头。特别是对于走出故土的成年人而言,自己的童年情结与当下的时间构成艺术的张力,越年长越喜欢回忆童年,童年情结越显出艺术之美。云南本土导演拍摄了几部这样的电影,导演的童年情结往往是与故乡情怀缠绕在一起的,故乡情怀则往往是通过儿童视角表达出来的。《俄玛之子》(2008年)是云南导演李松霖根据自身经历改编而成的。片中的阿水怀着心中的梦想走出了大山,其实也是导演对自己走出大山之路的回望。“俄玛”是哈尼语,是“最受尊敬的长辈”之意。《俄玛之子》是哈尼之子献给故乡的礼物,是哈尼之子对故乡精神上的守望,而这种守望是对童年情结的固守与强化。微电影《童年》(2016年)也是云南本土导演拍摄的,是中年之后的“我”回到故乡之后对童年的回忆,是“我”于嘈杂的尘世中怀念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纯真与无虑,童年是“我”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之心得到暂息的港湾。“我”以成人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也是“我”对童年记忆的重构,是“我”慰藉沧桑心灵世界的方式之一,是“我”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返乡之旅。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温暖欢欣的,有的童年是充满忧郁悲伤的。云南导演张穆的《许愿树下》(2014年)呈现的是缺失性的童年记忆,“我”在无尽的希望中等待在外打工的父母归来。“我”回首童年,既喜又忧,经过岁月的淘洗,通过“我”平淡缓和的语气可感受到童年痛苦的心灵体验已不如从前那般。片尾是这片红土地得到了开发,打工在外的人们纷纷返乡。这也表明了“我”对故土是持热爱之情的。“童年”这个词带给人的往往是天真、无虑、质朴等等,有的导演喜欢借“童心”“童眼”去发现被纯真所遮蔽的历史的苦涩,去建构集体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记忆。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云南时代史,用孩子的眼光观察历史,为厚重斑驳的历史增添了一份轻盈。《走路上学》(2009年)展现了云南怒江大山里的一对傈僳族姐弟对“走路上学”的渴望,从中透视了当地贫穷落后的历史本真;《幸福微笑》(2012年)中留守在家的赵小娟既要照顾弟弟又要维护舅舅的利益,但故事的背景建立在2012年云南大旱的历史事实之上;微电影《放心》(2015年)用孩童的口吻讲述了2014年10月云南景谷县地震后亲人去世给自己带来的伤痛,也歌颂了社会集体的温暖;《米花之味》(2018年)通过一对母女由陌生到和解的过程,体现了当下乡村生活中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微电影《彩云之交》(2020年)以儿童的眼光观察了上海交大在云南洱源帮扶脱贫的历史。导演以儿童电影为媒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复杂的历史经过儿童的目光过滤之后重构了历史的本来面貌。珠江发源于云南,珠江是两广地区的母亲河,其水流澄澈,正如初生的婴儿般纯净,它隐喻着云南的“童年”属性。除此之外,云南省内还有怒江、澜沧江、元江等大小河流共600多条。云南江河纵横、水系丰富、森林覆盖率高,仿佛人类童年生活环境的再现。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上看,云南与“东部社会”的文明发展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它正处于成长期,类似于童年的发育期。云南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发展上来看,都具有烂漫的童年属性,因此它在儿童电影语境内有了新的阐释。《戛洒往事》(2012年)中壮美如画的戛洒风光、乡村热闹的集市、葱翠的远山、蜿蜒流淌的小河、戛洒人随性的生活状态,阐发了“云南”与“童年”的同一性内涵。导演何瑞博立于云南本土,用儿童视角丰富了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
二、英雄情结
“英雄情结”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的沉淀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是代代相传的心理基因,对英雄的崇拜或英雄梦想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英雄是电影永恒的话题,作家、编剧、导演始终怀有英雄情结,钟情于塑造英雄人物。“十七年”时期的《鸡毛信》《英雄小八路》《小兵张嘎》等儿童电影塑造了一批英勇无惧、形象高大的“革命小英雄”。新世纪以来,英雄化的宏大叙事被减弱,电影中呈现了英雄的日常性、平凡性,但英雄“高大”形象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幸福微笑》(2012年)里赵小娟多病的舅舅被恶霸团长逼迫着演出,她挺身而出替舅舅演出;为了弟弟,妈妈让她辍学,她毫无怨言地在家照顾弟弟;她既要干农活、做家务,又要像成人一样安慰想念妈妈的弟弟。作为一名儿童,赵小娟做的一切即使是成人也未必做得到。她任劳任怨,甘愿付出,能文会武,上得了舞台下得了厨房,小小年纪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赵小娟的完美形象凝聚了编剧、导演的英雄情结,她也是新世纪儿童电影银屏上的小英雄。但小英雄的形象过于理想化,而成了思想教育的载体。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中不仅塑造了儿童小英雄,也塑造了成人英雄人物,最突出的当推教师这一类知识分子。《希望树》(2012年)中在云南丽江的一所小学义务支教三年的刘寅老师,没领一分钱的工资,且他自己到酒吧卖唱挣钱给孩子买肉吃,支教结束后,他又决定到另一个需要他的学校去;《大山里的曙光》(2014年)中在大山支教两年的王欣老师,还有让人敬佩的坚守岗位二十八年如一日的胡校长;微电影《尘》(2014年)中既要传授知识给学生又要做学生父母的校长。这些教师们的行为固然是受积极参与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信仰的体现,更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情结所致。他们都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别人的命运,去拯救别人于水火之中。他们是平凡的、英雄的,甘于自我牺牲,他们以自己默默的行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欲拯救儿童于水火之中的,电影内外除了教师们还有老板、导演们等等。纪录片《你一定不曾了解过的云南?》(2013年)中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山区学生的女老板有着英雄的侠义。《三姊妹》(2012年)的导演王兵、《小雅各布》(2012年)的导演赵大勇、《看世界:云南(微电影)》(2013年)的导演邵馨莹、《寸草安心》(2019年)的导演柴红芳等,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生活在云南贫困乡村里的儿童,他们把乡村儿童的故事拍成一部部动人的电影,其希望通过电影的力量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乡村儿童。电影制作完成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们的一个个英雄梦想,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临沧微电影《兄弟》(2014年)的导演晓渺关注点更是不一般,将镜头对准了乡村残障弱势儿童,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关怀。在一个看重演员颜值以及流量的时代,晓渺导演敢于向世俗的观念挑战,也是他英雄主义梦想的无意识体现。总之,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无论是导演还是片中的人物均有着英雄情结,这成为电影不可缺少的元素。
三、集体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一直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家国天下的情怀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集体情结,这点在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中也有所体现。《包裹》(2012年)中的青年教师吴老师网上发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当地的小学生,接着从全国各地寄来了一个个爱心包裹,书写了社会集体的人间大爱;像赵大勇这类导演之所以拍出《小雅各布》(2012年)此类电影,是因为他们有着集体主义认同感,相信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会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微电影《月光梦》(2017年)中的周利君在社会助学之下圆了自己的舞蹈梦,歌颂了集体的温暖;《滇梦》(2014年)讲述了上海教委支援云南元阳的故事,《彩云之交》(2020年)讲述了上海交大在云南洱源帮扶脱贫的故事,这两部电影都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集体力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集体情结已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价值纽带。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是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三个典型文化体现,电影中还能看出云南的边地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等等,在此不再分析。电影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电影也具有审美性,但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整体看重于意识形态的表达,少了一份艺术美感。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2.
作者:王东旭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