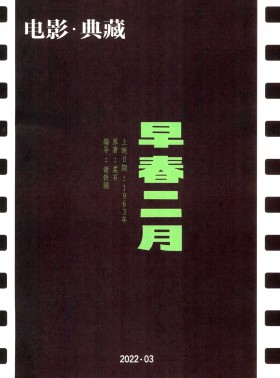回顾过去的电影教学,“蒙太奇”比其它电影术语更会被人曲解和滥用。每看到电影剪辑师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面切成一系列短镜头并连接在一起,就有人说是创造了一个蒙太奇。因此,有人根据“蒙太奇”(montage)的“构成、配置”的含义,简略地把蒙太奇称为镜头(或画面)的分切和组合。如果是在默片时代,这样规范蒙太奇的含义,应该承认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无声电影中,内在语言的形成过程完全取决于镜头的组接、对比和电影句子的组成。由内在听觉来加以补足的情况在音乐中也是存在的。在现代电影作品中,许多没有音响的优秀的空镜头,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音乐和声响的强烈的或尖锐的穿透力。这是从视觉上产生声音的联想,即“此时无声胜有声”。但是,随着声音在电影中的出现,内在语言的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内在语言,内在听觉能够补足和延伸影片的情节线索,并关系着对整部作品的判断、理解和评价。由此,伟大的哑巴一开口,声音毫无疑义开始成为蒙太奇的一个重要元素,并且和其它电影元素,———表现,造型,色彩,运动,剪辑轮流出任画面的主宰。 美国电影理论家李•R•波布克指出,“实际上,电影蒙太奇就是连续运用视觉形象(或音响),来制造情绪冲击力量。一般说来,蒙太奇是用来压缩或扩展时间或空间,并制造出特殊的情调。”如林赛•安德逊的《体育生活》(1963年出品),是描写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的生活的。为了表现这一需要身体碰撞的险恶的运动对主人公的影响,安德逊运用了几组表现这种运动的冲击蒙太奇。这些蒙太奇镜头由若干表现球赛时的身体的碰撞情况的片断性的长焦距镜头构成,并配上赛球时的音响———撞击声、呻吟声和骨折声。这样观众就被推进了球赛,并从感性上认识了这项运动某些残酷的因素。 如果对这组蒙太奇的理解忽略了撞击声、呻吟声和骨折声,仅仅关注几个画面的组合,我们将会捡到一根没有骨髓的干枯的骨头。爱森斯坦通过大量电影例子,证明蒙太奇不仅可以由镜头内容的主要特征、基本要素(中心刺激因素)组成,而且也可以由多个与之相关的特征———造型的、声音的、情绪等等特征(刺激因素)组成。他将这些刺激因素称为“泛音”(类似于音乐中的复调)。爱森斯坦认为泛音蒙太奇是各种现存蒙太奇思维形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且他总是始终如一地把“声音”当作蒙太奇的一个重要元素。当然,情绪也十分重要。 艺术中的情绪本身就蕴含着思想,这种思想往往比理性的分析和抽象的阐述更深刻感人。离开情绪是无法理解艺术作品的内容的。但对作品的感知不仅仅限于依靠情绪,因为我们是通过艺术来认识世界的。我们仅希望通过某个片断乃至全片的情绪表达,感染观众并使观众得到较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以电影声音因素中的音乐来说,它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音乐常常能绕过人们的智力活动,不诉诸智力而直接融入并撞击人们的心灵,它在听觉艺术中富有最强大的洞穿力、弥漫性和共鸣作用。一些缺乏阅读能力的人,会对许多著名的中外小说无可奈何;但他们听到一首感人的乐曲时,禁不住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只有情感才是音乐所要据为己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电影音乐可以分为“画外表现性音乐”和“银幕可见声源音乐”两类。约翰•威廉姆斯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出色地创作了主题音乐。沉郁忧戚的旋律充满了5度以上的跌宕起伏,表现了辛德勒的大智、大勇和觉悟的良智,为扣人心弦的情节增添了忧伤的魅力。音乐以它风格独特的听觉造型,与黑白摄影、色彩运用所营造的视觉造型,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这类音乐属于画外表现性音乐,它对于表现画面内容有鲜明的指向性。电影《音乐之声》中几首剧中角色演唱的歌曲,属银幕可见声源音乐。电影《砂器》中演奏的《命运交响曲》,表现了一个青年音乐家痛苦不幸的人生经历,与故事情节紧紧相扣,也应视为“银幕可见声源音乐”。这类音乐能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推动情节的发展,并赋于作品特殊的情调和鲜明的美学特色。对一部作品统一完整的构想,电影导演必须有内心视觉,以便一下想象出自己的整个作品。与此相似,作曲家必须由内心听觉,以便一下子能听到和想象出整个电影。譬如,从视觉艺术角度看,让角色的目光发挥巨大效能与逼真的可能性,这是电影艺术中最伟大的成果之一。目光交流与目光独白所具有的巨大表现力量,往往用来代替许多动作和对话。它是不能转述的,就象音乐不能转述一样,但它可以感觉到,可以理解,可以调动起人的情绪。同样,从听觉艺术角度看,电影音乐也可以具有犹如目光独白和目光交流的显著效能。 电影《简•爱》中有一段精彩的对白,这段对白是在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的伴奏下进行:“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于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钢琴细腻流畅地表达了女主人公丰富优美富有自尊的内心世界,清新朴素的颤音诗化了语言的韵味。主题音乐造成了蒙太奇的情感冲击力,给人物宣言式的话语注入了热烈的极富个性色彩的因子。这段主题音乐的巨大作用完全可以和目光特写的效能相媲美。主题音乐的洞穿力、弥漫性和强烈的共鸣作用有着无法抗拒的艺术力量。 这类先确定一个音乐主题,然后在整部电影中反复运用的作法虽然毫不新鲜,但在精度和创造性上很有讲究。获奥斯卡最佳音乐奖提名的《魂断蓝桥》,它的主题曲《一路平安》动人心扉,催人泪下。这支曲子能激起人们经过升华的纯洁的情感。 运动起伏的旋律,遵循着音乐家发自心灵深处的深沉的回声,以柔美的色彩斑斓的情绪,造成了一种感情和另一种感情的交替。正如剧中男主角罗依在克劳宁家的舞厅对玛拉所说:“记得吗?我们到哪儿,这支曲子(《一路平安》)都跟着我们,今天晚上跟到了这儿。”它以无以伦比的美感和深挚惆怅的情愫,成为古今绝唱。许多优秀导演越来越迷离那种更深地潜入人们心灵的电影,其中重要的原缘之一,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音乐这根魔棒的巨大威力,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电影场面的效果主要来源于摄像机的运动和音乐的伴奏。在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里,一再出现的主题音乐是吉奥瓦尼•福斯科谱写的一支富有强烈节奏感的旋律。在影片的开场戏里,这个主题即已完整的出现,并成为这部影片的灵魂。它有它自己的活动和基本的节奏结构,它常常配合着雷乃最喜爱的技巧———流畅的移动摄影。在影片将近结尾的地方,女主人公从咖啡馆里飞跑出来,他追着她。当摄影机跟着她活动时,音乐起着决定速度的作用,也就是决定着蒙太奇运动、剪辑的节奏。同时,使观众清楚地回想起这个女人遭受过的全部苦难。由于音乐主题在整个影片中起着决定运动起讫的作用,所以碰到这样的场面,观众期待着运动:演员的活动速度,摄影机的运动,场景剪辑的节奏,———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由始终保持着其本身完整性的音乐来决定和维持的。所以音乐对作品情调的引发、蒙太奇节奏的确定的作用,决不亚于任何其它电影元素。#p#分页标题#e# 因《大白鲨》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维尔纳•菲尔兹,被年轻导演亲昵地称为“剪辑大妈”。她在谈到电影音乐时指出:“提到音乐,这需要同导演合作。摄制《大白鲨》时,我是和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起干的。我们放映影片,商量、讨论音乐应该在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互相交换意见。应当说,威廉姆斯的决定可能是最关键的。配乐之前,它就是一部好影片,但是他的配乐确实使影片大为增色。斯皮尔伯格对鲨鱼和船相互追逐的场面的音乐有些非常特别的想法,这些要靠威廉姆斯去写他的音乐。同时,我们都去资料馆听音乐,选择其它合适的音乐材料。”许多影评家指出,关于鲨鱼的音乐,是使鲨鱼成为重要银幕形象的要素,也可称为“鲨魂”。成功的鲨鱼形象,又构成人与鱼、人与大海的强大张力和冲突。音乐又使影片节奏流畅,险象环生。用其它方式,很难塑造鲨鱼的形象,而音乐却鬼斧神工般地完成了。同时,“剪辑大妈”这段话也提供了电影配乐的几种方法。一种是从备有大量音乐选段磁带的音乐资料馆去挑选。影片剪辑时,剪辑师把需要配乐的场面配上适当的音乐选段磁带。另一种方法由作曲家观看已剪辑好的影片,仔细记下每个需要音乐的场面的准确长度,然后他为影片谱写音乐。第三种方法是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许多导演选择这类方法。电影同期录音或后期配音的对白、解说、音响效果,以及用各种方法制作、配置的音乐,都是电影声带的主要元素。各个镜头、场面和段落经过剪辑之后,再把包含上述各种音响元素的多种声带进行剪辑,以匹配和衬托视觉元素。 对音乐与画面的和谐的追求,对音乐与时间、空间关系的处理,始终是电影艺术家关注的焦点。 爱森斯坦在1926年就尝试用声音来为电影服务了:音乐家梅赛尔为《战舰波将金号》所作的曲子,摆脱了用音乐来解释画面的局限性,使音乐和视觉形象统一。爱森斯坦追求音乐运动和造型结构运动的协调,并努力使两者的运动在同一基础上进行。爱森斯坦对电影视听结合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然而,他过于注重画面的构图,使他最后的几部电影有着明显的减慢动作速度的倾向,因而就剥夺了动作的活力。在《伊凡雷帝》里,声音与形象的交互作用迷失在一连串静态的场面和繁复的象征中。爱森斯坦企图表达的意义太多了,因此失去了视听结合中至关重要的运动特质。 普多希金根据自己的导演实践深刻地指出:“电影拥有声音和画面的双重节奏,善于掌握这种双重节奏所提供的可能性,乃是解决有声电影的基本关键之一。”在执导影片《逃兵》时,为了表现“象征着游行队伍尽管没有取得有形的胜利,却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他和作曲家沙波林决定改变音乐通常只是与画面平行发展的单调的伴奏(音乐仅仅是解释画面),而把连贯的庄严肃穆,充满胜利信心的工人进行曲,从头到尾坚定不移地不断加强。这样处理,可以使第二条线索,即在声音发展的线索中,对画面中所发生的一切,作出一个主观上的深刻的评价,以暗示给每个观众。 这种声画异步的创新举措,被后来的电影工作者称作电影修辞或处理声画关系的著名准则,在有声电影史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对开拓电影艺术的表演空间和表演时间,起到了别开洞天的作用。数不胜数的优秀电影以它声画异步的浑然天成的巧妙运用,奏出了电影艺术精彩的华章。 我们在分析强调电影音乐的同时,对电影其它的声音因素———话语、动物的声音、自然声等,同样要予以高度重视。它们同样是构成蒙太奇,创造艺术形象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元素,同样是使有声电影成为“另一种完全独立的艺术”(巴拉兹语)的重要元素。为了阐明音响作为电影的一个主要元素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去看放映一个去掉了声带的影片的场面。一旦没有了声音,无论画面拍得多好,剪辑得多好,仍然不再有真实感,因而失去了感染力,失去了影片在时间的“链条”中展示客观事物的特性。影片的速度似乎减慢了,结果常常像看到了一系列照片。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历来对声音十分关注。他自认为他的音效具有非常确切的意义。在影片《群鸟》中,他为了突出鸟的聒噪,就以鸟的叫声取代了音乐。他不仅利用乐队来演奏音响,而且还借助电子模拟器来模拟鸟的叫声、振翅声,以获得最强烈的紧张效果。 人类爱鸟、宠鸟,而又囚禁驯养鸟,结果却遭到鸟的攻击和报复,甚至演变成人鸟倒置,这岂不是一个怪诞的寓言体?其中的内涵不是发人深省吗?希区柯克的这些超越常人的前卫思想,通过独特的声音效果,使观众触摸到艺术的智慧火花。 查尔斯•F•阿尔特曼在《精神分析与电影:想象的表述》中论证了声音与画面的关系:“即使是古希腊人也知道,没有埃科的故事,那喀索斯的故事也是不完全的:是声镜(audicmirror)使视镜(vidiomirror)完满的,实际上,这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为影像与声音的关系提供了漂亮的解释。电影依赖声音的反射,就像依赖光的反射一样。如果将电影比作那喀索斯的视镜,那么也必须把它同埃科的声镜联系起来。”阿尔特曼引述这则传说,试图用精神分析法说明镜像阶段中的主体的一体性不过是以把影像误解为现实的代价获得的,有声片的一体性也是用不实之言买到:依附性的回声被当作是再现在银幕上的人物的实际声音;而事实上,以当代的技术条件能够符合任何具体影像的录音,并来跟着那个影像出现在影片上。他的论述,从某个角度会引起我们对电影现状的思考:许多平庸的、软弱无力的、毫无个性的音乐和声音,确实毫无“美妙”和“创造性”可言。我国年产电影150部左右,2004年国产电影超过200部,电视剧超万集,但像《英雄赞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祖国》,像《少年壮志不言愁》、《好人一生平安》,这样唱遍大江南北的影视歌曲,却寥若晨星。音响造型与视觉造型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就十分密切,“戏不够声音凑”的情形在生产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向影视音乐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要求,他们必须要深入生活,必须要有厚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富、深刻的情感体验能力。作曲家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多部影片创作音乐。#p#分页标题#e# 为了采集民歌素材,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采集民歌素材。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至今仍流唱着的优美曲调都是他艰苦收集,精心提炼、加工创作出来的。因此,影视的音乐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与社会保持积极的关系,经常深入生活的源泉,对电影作品要有深刻独到的感受力,这样才能塑造出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有震撼力的音乐形象。 路易斯•布努艾尔在《电影的元素》的扉页中写道:“一部电影就像对一个梦的不自觉的模仿。 黑暗慢慢笼罩影院的情景就像把眼睛闭上的动作。 然后,在银幕上,就像在人的内心一样,开始了进入下意识世界的夜间航程。渐显渐隐的手法,使音象像在梦中一样出现和消逝;时间和空间变得很灵活;可以任意收缩和扩展;时间延续的年代顺序和相对价值不再同现实吻合;首尾呼应的情节可以延续几分钟或几个世纪,从慢动作到快动作的转换加强了两者的冲击力。”这就说明每一部影片都具有自己处理时间与空间的独特方式。电影中的时间可以创造,可以改变,甚至可以消灭。电影可以使时间停止,使时间延长,也可以使时间倒转。电影中的时间同造型一样具有可塑性。电影形式的时间限度实际上是无限的,这就赋于电影艺术具有巨大表现力和灵活性,而这种表现力与电影中声音的运用有密切的关系。 阿仑•雷乃导演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年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剧中人物对话和各种音响的发生时间,不知是在“去年”,或许还是不在去年,人物所处的时间是死的时间、木乃伊化的时间。影片的故事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在瞬息万变的意识流中展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宣称:这部影片的获奖是为它“对电影语言的贡献,以及它在表现这样一个世界时所显示的风格上的异彩,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的东西与幻想的东西共存于一种新的空间与时间的向度中。”阿仑•雷乃运用音响等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处理电影时间和空间的方式。 这部电影的编剧阿仑•罗勃-格里叶赞同说:“我更看出雷乃的作品企图建造一种纯粹心灵上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感情和生活的节奏。”日本电影《砂器》结尾是由三组镜头组成的交叉蒙太奇:一组镜头是青年音乐家贺和英良在指挥乐队演奏他创作的《命运交响曲》;一组镜头展现了他从幼年到青年的痛苦曲折的人生;一组镜头是两名日本警视厅的警察,守候在剧院门口,准备在交响乐演奏完毕,立即拘捕杀害自己的继父三木谦一的嫌疑犯贺和英良。 三组镜头反复交替出现。演奏交响乐所用的时间是“放映时间”,也是“物理时间”,但是观众感知的过程并不限于听交响乐的时间,这正是电影的时间感觉的本质所在。在这里,剪辑师出色地运用了叠化音响剪辑--一个场面的伴音和前面或后面的场面的伴音相重叠,改变或丰富了互无关联的视觉形象,来连接从一个场面到另一个场面的动作,并加快影片运动的节奏,把影片的情绪推向高潮。“艺术是把打击力放在最后的”。而这强大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来自音乐,音乐的节奏,和音乐对时间空间的改变。电影蒙太奇连接的是纪录在拍好的镜头中的时间。蒙太奇能把载有不同浓度或相同浓度的时间的大大小小的片断粘接在一起。而这些片段的结合能使人获得对时间流逝的新感觉,并产生新的时间范围。卓菲姬•丽萨在她的《影视音乐美学》中,将这种音乐处理方法用艺术心理学的语言做了这样的概括:“视觉的观察想象被视觉的幻觉想象所补充,而这种视觉的幻觉想象是借助于听觉的观察想象才被创造出来的。”在《砂器》这组交叉蒙太奇中,有对银幕上直接发生的感知,对过去的感知,和对未来动作发展的预料或预测,它们一起决定着感知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框架。正是通过音乐,蒙太奇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达到了在时间上的延长,并在思想内涵上揭示了像贺和英良这样出身低贱的人,要挤入日本上流社会,最后的结局会像海滩上的砂器,被无情的海浪击得粉身碎骨。这组富有特色的蒙太奇也验证了波布克的论断:“一般说来,蒙太奇是运用来压缩和扩展时间或空间,并创造出特殊的情调。”《公民凯恩》不愧为电影声音的佳作。早在四十年代,它就在声音造型上取得了很高成就。影片充分运用电影多时空的独特表现力。从1870年凯恩的童年,一直追随到凯恩之死,时间跨度达70年之久。这部被誉为“第一部现代电影”的杰作,它的成功是与创造性地运用多视角、性格悬念、音响、音乐、景深镜头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看到无论在音乐中,还是在电影中,改变时间坐标是基本结构手法之一。 在音乐中,这常常通过音调结构的改变。音乐的音调与人类的感情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等形式--在逻辑上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也可以说,音乐是人类情感生活和心理活动的音调摹写。在电影中,改变时间坐标则要借助蒙太奇手法。对艺术作品中给时间以长短的估计取决于感受的内在定向--期待、悬念和解决。一部作品中实际时间长短和感觉中的时间长短的比例总是同这部作品的性质和时间结构有关。同时,情绪越专注,就会越觉得时间流逝的迅速,因为这时在感受中失去了和客观时间的对比。在电影艺术中,单位时间内所体验的事件的数量和强度,作品的情绪饱满度,与对时间感知的快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存关系。 研究和把握这种依存关系,对于运用蒙太奇,运用音乐、声响来开拓时间的限度和空间的容量,加强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度,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对电影蒙太奇或音乐形式的逻辑的感知的规律,是以人在影象或声音消失后仍能把它们保留在记忆中这一特点为基础的,光影还可同时留在人的视网中。留下的痕迹仿佛叠加在接踵而至的音响或影像上面。 正因为如此,音响虚线--单个音符的更替就能在感知中联成实线,联结成旋律。而镜头的更替,蒙太奇景别的剪辑和交替,会被感受为统一的运动。所有的不平展之处都在感知的过程中,被内在的视觉和听觉加以展平。#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