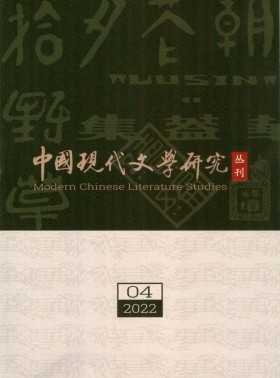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整个大陆文坛侈谈爱情,对描写讳莫如深之时,《现代文学》(1)小说却非常大胆地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青春期少年早期性教育问题的作品,《母亲》《儿戏》《寒流》《寂寞的十七岁》《壁虎》《释善因》《藏在裤袋里的手》等小说都可以被视为当时海峡两岸探索早期性教育问题的力作。
区分青春期与儿童期的界限是性的成熟,“对于男性来说,性成熟的标志是遗精,(通常在夜间睡眠时遗精);女性是月经,即第一次来月经。以性成熟为核心的生理方面的发展,使少年具有了与儿童明显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2)青春期到来时,由于自身第二性征的凸显,通常会使少年格外关注异性的第二性征。“孩子进入青春期,与异性接触时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悄悄地关注异性。关注往往只是停留在外表上。”(3)如小说《母亲》(4)中那十多岁的、热衷于偷看离异女邻居的裸体的男孩,在他妈妈为他没有回家而牵挂操心的时候,他却躲在离异女性的家门旁边,等待那位时髦、漂亮的女性回来。因为那位女性回卧室换衣服的时候丝毫不避讳正在成长发育的小男孩,会让自己赤裸的身体被小男孩一览无余。《寒流》(5)中那十三岁的男孩疯狂地迷上了商店裸体彩绘女像,他“经过店门,迅速地望向店中挂在壁上的一面镜框。他的小小的心鹿撞着,耳根泛出了血红。那是一张裸体女人的侧像,她的肌肤洁白如玉,她的一头金发像狮子一样披下来,歪侧着头,凄迷着眼,她的两手淫荡地抚按在乳房上,她的一条丰美的大腿收向小腹。这孩子就站在门外望着她。为着要看她,他已经在学校苦待了一日;其实,无论何时,只要一闭拢眼睛,他都能记得起她的裸体的每一部分,然而他更要每日亲眼见到她”。作为刚刚进入青春期男孩,他们对于异性的好奇心,尤其是对女性的第二性征的好奇心,都源于青春期特有的、无法控制的生理冲动。《寒流》的那个男孩原来是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孩子,每天放学后,他跟着同学一起在火车道的铁轨上比赛,看谁走得最久。“他们每天这场竞赛的高潮——当跑过一座长铁桥时,忽听见一声汽笛哀鸣,于是便一齐兴奋复紧张地尖叫着,加速地跑至对岸,然后纷纷像小鸟一般跳到土堤下……”,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他便不再加入同学们的行列了,“他忘记了寒冷,因为他正迷醉于另一件神秘的游戏。那个游戏就在大街的转角等待他,他还不知道那是比逃火车更危险的游戏”。原来他偶然发现在一家商店里有一个裸体女人的彩色侧像,而那次偶然的经历,使他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突然变成了早熟的少年。看了裸女图像再回到家中,已经过了吃饭的时候,他撒谎说被老师罚站。由于青春期无法遏制的生理冲动,他夜夜梦遗。因此,每天夜里到了上床的时候他都感到害怕。他下定决心要不再经过那家店,不再看那幅画。然而他的生活已经失控了。上课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忘记了周考,听课的时候他居然用笔在本子上画裸体女人。当本子被老师收走后,他很想让老师发现自己的画,“失去了作业本后,说也奇怪,他竟然感到一阵庆幸,接着是一阵欢喜。但是他也感到恐怖……解脱了!他想,再也没有那自己想象的罪恶来戕害我了,再也没有那毒蛇似的妖娆身段来盘缠我了”,很遗憾老师没有发现那些裸画。而他在放学回家的时候因为神情恍惚,差点儿被火车轧死。劫后余生后,“他蜷伏在堤脚,许久不动,直到火车不复听到。然后,他从地上坐起,他放声大哭起来”。青春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它也是人们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理机能逐步增强,内分泌机制完善,心理的变化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相应的发展,迅速走向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个过渡期。小说《寒流》中的男孩的表现从某种角度来说属于青春期少年特有的、由生理失衡和心理失衡引起的心理疾病——“青春期综合征”,这一病症具体表现为“睡眠规律不正常,白天精神不振,上课易瞌睡,大脑昏昏沉沉,夜晚卧床后,大脑却兴奋起来,浮想联翩,乱梦纷纭,性冲动频繁,形成不良性习惯过度手淫,并且难以用毅力克服,逐渐出现频繁遗精、滑精……由于上述种种生理失衡症状困扰着青少年,造成青少年心理失衡,表现为忧虑、紧张、抑郁、烦躁、消极、敏感、多疑、自卑、自责、表面上强打精神,内心充满困惑和痛苦,无奈和彷徨,甚至产生厌学、逃学、离家出走、早恋、性犯罪,甚至感到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好的念头”。(6)小说中的少年每天在焦灼中度日,“他读过生理卫生,因此他晓得害怕——已经接连来过四个夜晚了……想到生理卫生书上教导的预防方法,他便将一床温软的红绫棉被推向橱下,跌落在地板上。在这寒夜中,他将只取一张轻盈的鹅黄洋毯遮盖。他希望今夜不会再来……他被侵入毛毯的寒气冷醒……他发现又来过了……他的那双纤小的肩膀徐徐颤动,继而像一双小兔子般一起一落,但并不像寒冷而起的瑟缩,那比瑟缩尤激烈。他在哭泣中”。在天气预报说有寒流的那个夜晚,他选择了脱光衣服坐在椅子上睡觉。“今夜那错误将没有机会出现,呵,你们那陷害我,诱骗我,使我不自觉地掉进陷阱里去的睡眠和温暖,你们听好,今夜你们将得不到机会……”夜里,“他的头已昏眩得抬不起来。他从胸口中猛烈地呛出几声咳嗽,他觉得喉管中有火焰在燃烧,全身都在燃烧……”当今社会,青春期早期性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官方教材和课程,有网络图像和视频,还有各种级别的影视、图书资料,所以,如今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仅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而且能够通过所习得的生理知识,科学、有效地排解因为青春躁动而产生的各种生理疑惑和心理问题。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整个华夏大地还是“谈色性变”的时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既不能通过校方教材掌握青春期生理、心理特点,也很少能从恪守封建观念的家庭中获得长辈亲传。所以,当青春期的生理成长高峰到来,青春期特有的各种心理发展问题也纷至沓来时。青春期的他们孤立无援,惶惶不可终日,往往只能凭着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寒流》中的男孩在没有任何外来因素指引疏导的情况下,盲目地伤害着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小说《藏在裤袋里的手》(7)中的吕仲卿则更加不幸,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他在心理成长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发展成了心理畸变的伪男人。吕仲卿小时候无意中看到女佣荷花洗澡,荷花抓住他的手往白花花的臀部按,还说“你摸摸看……”。他被吓坏了,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离开过妈妈的房间和床。他做过很多梦,“梦到手被捉住放到一个痴白肥大的女人的臀部上。他踢着,喊着,总也挣不开……自此以后,他见了女人就想躲”。幼年的经历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人生。16岁第一次结婚,但是连盖头都没有揭开,他就跑回来妈妈的房间。妈妈去世后他发现了妻子玫宝,在玫宝那里感受到了跟妈妈一样的舒适、安全。可是玫宝不像妈妈那样呵护他,她很反感,总是呵斥他,跟他分床睡,每当他想靠近她,她都会怒斥他。玫宝在家跟朋友打桥牌,把他赶出门。他走在大街上,手藏在裤袋里。然而在他被赶出门外的这一天,他仿佛听到了“一缕极熟悉的声音,邪邪的召唤他:‘你摸摸看——你摸摸看’……吕仲卿陡然觉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插在裤袋里的手猛拔了出来,他朝着那团紫光踉跄地奔了过去。”结果他被人当成流氓围着一顿揍,而被揍之后,“这晚吕仲卿睡得十分安稳……”。毋庸置疑,吕仲卿的心理是病态的。而他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心理畸变者,究其原因,青春期所遭遇的非正常性启蒙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寒流》还是《藏在裤袋里的手》,都昭示了当时社会在青少年性教育方面的失误。由于教育部门和家庭以及社会有关方面对青春期教育的忽视,对青少年早期性教育的的疏于督导和防范,导致了青少年在青春期生理与心理发育的不同步。而心理发育相对滞后则使青春期综合征等心理疾病产生的概率大大提高了。
如果说家庭和社会对青春期少年性朦胧意识的疏于督导和防范导致了青少年青春期综合征的形成,那么,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约束下形成的“性行为丑陋、肮脏、可耻”的观念意识则严重扭曲了中国人的婚姻道德观念。对于传统旧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性行为无关其他,仅仅是一种传宗接代,使得家庭血脉得以繁衍不息的生理行为方式。在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以非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是不洁的,可耻的。倘若有人以性行为作为取乐、享受的娱乐方式,那么就会陷入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中,成为被社会整体排斥和鄙视的对象。由于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意识横行,男性在性行为方面的享乐往往比较容易被接受,而倘若女性坦然享受性行为所带来的快感,则会被列为放荡、无耻、堕落之流。因此,《壁虎》(8)中的大嫂会因为耽于肉欲而被视为“祸水”,“没有人,甚至我的父亲,对她说些欢迎的话,可是她却满不在乎的摆动她丰满的身体和挥霍她已经狼藉不堪的声名。朝北的弓形白璧的尽头,有三两只怪肥大的黄斑褐壁虎倒悬在墙上,这女人踱到那一角的步姿使我萌生起她一如壁虎。她像不太有灵魂,她却爱生命,爱到可耻的地步。她已成就的少妇风情和微有些倦态使我感出她是生活在情欲里”。对于16岁的主人公来说,大嫂耽于肉欲的堕落是众所周知并非常令人不齿的,“我感到我的大嫂根本不值得去恨她”。小说中主人公因为轻度肺痨和丧母之痛,“在我脆弱易感的性格上有了极度病态夸大倾向”。而她大嫂入门后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氛围,“每天晚上,当我咳得醒过来时,仅只是走廊对边,大哥房里细碎的传来笑浪,我感到无可比拟的羞辱,一种人的尊严被撕成片片……大哥的迷恋罪恶使爸爸痛心,而他决意辞去待遇丰厚的工作跟大嫂排遣时间的方式震撼了我们威望的门族。他们没有精神力量和一切秩序,只有披满酒与情,如同赤裸的壁虎,无耻存活”。虽然传统封建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早已深入整个家庭,然而,人类的本能在过分压抑之后终于爆发了,那位堕落、无耻的女性以实际行动高调宣告的美好以及带给女性的愉悦“……空酒瓶、香烟灰、腐朽的霉味,不堪入目的彩色照片,脏布片,衣服构成房内的全貌。我透过蒙蒙飘尘中看到了床上两个熟睡的躯壳。他们斜卧着,大哥纤细的胳臂压在女人敞开的前胸,他的另只手臂环住她裸着的腰间”。自以为深受骚扰的、恪守封建礼教的人们经历了身心煎熬之后,终于被本能欲念打败了,首先是从省城学成归来的大哥全面覆灭,而后,“我的灵魂向上的幺哥带着忏悔回神学院……更惊人的是我的誉满门族的二哥教我弹琴的手冷而且颤……爸爸和我在机场挥别了他,只有我知道二哥决意留学且如许仓促离家的真正原因。”原本立场最坚定的女主人公在接触过爱情婚姻中灵肉结合的滋味后开始动摇了,结婚后“竟渐渐地因着我的丈夫的细致体贴生活得十分快乐起来……”曾经,她对大哥大嫂的行为深以为耻,然而,“我结婚了,可怪的是我竟过着前所不耻的那种生活。我现在只是盼望,盼着秋天赶快过去,那时,即使是廊下白墙上也不会有嘲笑我的可恶的壁虎了。并且最重要的,我需要毫无愧怍去接受我的丈夫的温存呵!”而被大嫂那个“耽于肉欲”的坏女人破坏了门风后,他们整个家庭都产生了巨变。“以后的两年,幺哥回到镇上的教堂为上帝服务,我也学着信起教来,我们又把嫁出的姐姐接回来住……那个案子的结果是由父亲两年的牢狱生活抵消。”如果说这篇小说呈现了传统道德的性压抑和现代观念中性泛滥的交战,那么主人公的大哥无疑可以被视为是二者交战的牺牲品。大哥被现代性泛滥俘获,而二哥无情压制了自己的本能欲望,成为传统观念的忠实信徒。而“我”则比较幸运地成为了二者调和的收获者。幺哥和二哥的挣扎,都是具有当时社会代表性的。已为人妇的姐姐的归家,似乎也蕴含着某种传统道德观念压制失败的深意。
如果说《壁虎》描写了一位女性逐步改变了自青春期开始形成的“性丑陋”的意识,那么《释善因》(9)则用另一种方式阐明了传统性观念对青春期少年人生的荼毒。释善因和尚15岁出家当和尚,修行24年,过着清心寡欲的无性行为生活。然而,他最终并没有能够躲避红尘。在修行了24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脱下了僧袍,重新返回了尘世。而他当和尚的原因是他父母至死都不知道的。他15岁的那年,邻居家办丧事,“两侧的布帆上,挂了好几幅地狱万象图。见了这一神秘的景象,他满怀童稚的好奇,到里面参观。灵桌的右侧停着一具猩红的棺木,盛着已入殓的死者。他不甚了解‘死’是什么……他被悬在左侧布帆上的一幅地狱万象图所吸引住……无数赤裸的男女,正承受着形形色色的酷刑……最令他悚然而栗的是有一个赤裸的女人头下脚上地塞入石磨中,研成肉酱,旁边注着两个蝇细的小字:淫妇。而另一赤裸的男人则被一群小鬼押着,等候受刑,旁边注着:奸夫。他瞧着,瞧着,想着自己一年以来在被窝中所犯下的罪孽,额上不禁冷汗涔涔,脸色泛白。”青春期少年普遍具有的生理反应被封建观念荼毒为必须下地狱的淫贱行为,于是,在“看了地狱图的那个夜晚,他又见到那赤裸的女人。但是现在除了裸女之外,还出现了无数青面獠牙,手执钢叉的小鬼,环伺着他。那裸女频频向他招手,要他过去,而小鬼们圆睁怪目……他肉体中的火焰被那女人的手煽得更为炽烈,无法遏制,便一步一步偷偷向那裸女移近……然而小鬼们却猛扑过来……小鬼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押到石磨那里,头下脚上塞进去。他大喊一声,蓦地醒过来……翌日凌晨,他父母未起床时,他离家出走”。后来,他父母到寺庙中找到他,无论如何劝解,都不曾动摇他自我救赎的决心。一年后他母亲抑郁而终,三年后他父亲也伤心而逝。虽然内心也充满了自责,可是仍然没有动摇他通过修行来避免遭受地狱折磨的决心。然而,在他潜心修炼了24年之后,某一天,他在梦中看到了一对偷情的男女,并在梦中杀死了那个男人,扑向了那个满脸惊恐的女人。梦醒后,“他感到下体有些异样,伸手去摸,黏湿湿的……他跪在床缘,双手抱头,俯在床上。‘想不到二十四年的苦修不过付诸流水而已,并没有使我参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我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因此,时隔20多年之后,他终于回家了。然而,传统封建的性观念已经给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20多年的孤独岁月,含怨而死的父母双亲,彻底葬送了他本应幸福完满的家庭。无论是传统封建性观念,还是佛教思想的虚空观念,都无法拯救陷他在人性本能压抑下的灵魂。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两性之间的是神秘的。因此,如果没有正确地引导,好奇的青春期少年往往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做出一些令他们追悔莫及、遗憾终生的事情来。《儿戏》(10)中那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这样的,由于对懵懵懂懂却又充满了好奇,加之讨论过某些父母曾经不小心落入他们眼中的某些可疑行为后,他们思索着男女之间可能有的那种神秘的交流,决定尝试并立刻付诸实践。结果,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青春期女孩葆玲,带着一心渴望超越妹妹的青春期少女美珉,走入了青春期男孩世宇的房间。对故作了解的葆玲亲自导演了一场儿戏——指挥着美珉爬上世宇床,并脱去世宇的衣服。起初世宇因为睡觉被打扰而生气地反抗,而后来,当第二性征明显的青春身体互相摩擦后,他对异性的触摸产生了本能的生理反应,结果,两个怀着青春生理冲动和本能欲望的少男少女纠缠在了一起,当美珉因处女膜破裂的痛叫声把所有的人吵醒时,葆玲所谓的秘密游戏就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相对于《儿戏》中的少男少女的初次性经历来说,《寂寞的十七岁》(11)中的17岁少年的初次性经历更为悲惨。小说中的少年因无法排遣由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合力共同造成的巨大压力而失身于某中年同性恋者。而这种不被世俗接受的、另类性行为的发生,无疑会带给那青春期少年终生无法消除的心理阴影,甚至可能从此扭曲少年的性观念,使他踏上荆棘丛生的不归路。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我”是家中所有的孩子当中学习最糟糕的一个。爸爸为此非常愤怒,总是训斥我。妈妈也总是唠叨。回忆起整个17岁的生活,因为学习不好,被父亲责骂,被母亲唠叨,被同学排斥,被兄弟嫌弃,这一切使他感到悲观绝望,事发当日,他在体育课上被逼迫上单杠,结果摔得鼻青脸肿;大考前,拒绝了班里开放的女生的诱惑却又于心不安,于是写信道歉,而这封信被放大并公然贴到了黑板上。他因此成为全班的笑料,还与同学杜志新发生冲突。他“跳上来叉住我的颈子把我的头在黑板上撞了五六下。我用力挣脱他,头也没回,跑出了学校。”因为错过了考试,爸爸暴跳如雷。他的心情没有人明白,在这种境遇下,17岁的少年感到活着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他用手表跟弟弟抵押了50块钱,在外面游荡游荡,最终,孤独落寞的他遇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把我的两手捧起来,突然放到嘴边用力亲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有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我应该挣脱他逃走,我应该大叫大喊。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坐在他旁边没有动,他搂着我的脖子对我说他喜欢我,他要我跟他好……你不晓得我那时心里有多懊丧,不要怪我,我什么都答应他了,只因为他那时搂着我低低地说了一声:‘我喜欢你。’真的,无论是什么人在那时在我耳边温柔地说一句:‘我喜欢你。’我什么事都无所谓了。我不喜欢那一套,我厌恶透了,我的脸触着冰凉的草地时,我的胃在翻腾。可是我什么都答应了他,只因为他那时对我好,我寂寞。”他是一个处于青春期逆境中的可怜又可悲的人物,是一个被家长、学校、社会、世俗的眼光、扭曲的心灵、变态的行为、被妖魔化的西方的思想观念共同促成的、时代的产物。是两性相爱的自然产物,然而,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的歪曲和否定,很多中国人都无法正视婚姻生活中的两性生活。尤其是从小被灌输了“性丑恶”观念的女性,倘若感受到了的快乐,便会自动将自己列入淫娃荡妇之流,使自己饱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如《壁虎》中的“我”,看到“我们阁楼廊下的白璧间,总有三两只或好多只黄斑纹的灰褐壁虎出现。
当夜晚我由我的丈夫极其温柔地拥着我走到我们的卧房时,这种卑恶生物总停止它们的爬行,像是缩起圆睁斜狠的小眼特意对向我。每当这时,我都会突然自心底贱蔑起自己来,我始而感到可耻的战栗,最后终是被记忆击痛”。虽然别人早就告诉她,结婚的日子“是另一个奇妙的开始,因之自然也能忘掉被迫记忆着的以前许多事”,然而“我”却无法安心接受,甚至为此背井离乡。虽然“我的丈夫并不因为我的执意离乡使他放弃那份可观的祖产而对我减少爱情”,可是她对于自己居然能够在中得到满足和快乐是无法释怀的。对她来说,她所屈从的那种愉悦感是与自己所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她的遭遇,在“存天理灭人欲”封建观念当道的传统社会中绝不是个别现象。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才会广泛出现如《寒流》里那样的,为避免梦遗不敢睡觉,甚至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逃避生理冲动的少年;才会有如《儿戏》中那种在好奇心驱使过早尝试生活的男孩女孩,而更多的应该还是类似《释善因》里那种在世俗观念、封建传统或宗教迷信影响下,完全否定青春期生理欲求合理性,主动承受身心煎熬和肉体折磨的显性和隐性的修行者。青春期是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青少年生理上的急速发展与性冲动的无法遏制,都需要正确的引导。然而,中国封建传统的性观念无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客观生理现实,无情压抑和打击人的本性和生理本能,最终导致了中国性教育长期以来都处于极端保守、落后与愚昧的状态中。而《现代文学》小说作家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够冲破旧道德、旧观念的束缚,将一向被有意排除在文学视野之外的青春期性教育问题堂而皇之地引入文学殿堂,不能不说是极具有创新精神的勇敢行为。
作者:徐英春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b65);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ZZ013)。
注释:
(1)台湾《现代文学》创刊于1960年3月,公开发行了13年,出版了51期,1973年因经济原因第一次停刊。1977年得到经济支持复刊,出版22期后,1984年第二次停刊。除了诸多优秀的原创性的小说,《现代文学》还系统地、大量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文学潮流。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加缪、沃尔芙、乔伊斯等直到80年代才被大陆广泛推介和接受的西方现代派作家都曾经被该刊以评介专号的形式郑重介绍过。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昂、施叔青等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都是从这个刊物起步并成长起来的。
(2)(3)(6)百度百科
(4)王文兴:《母亲》,《现代文学》1960年第2期。
(5)王文兴:《寒流》,《现代文学》1963年第17期。
(7)白先勇:《藏在裤袋里的手》,《现代文学》1961年第8期。
(8)施叔青:《壁虎》,《现代文学》1965年第23期。
(9)郑潜石:《释善因》,《现代文学》1964年第21期。
(10)於梨华:《儿戏》,《现代文学》1969年第37期。
(1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现代文学》196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