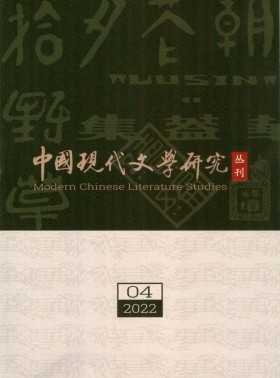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一)
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就套用了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叙事由主人公汪中复仇始而终于革命,完成了一条从复仇到革命的成长之旅,从复仇到革命的转换意味可以与成长作同义置换。这种成长因为有漫游的过程存在,有个体人生选择和生命实践的主体性参与其中,对社会不义性质的判断似乎被试图放置于漫游经历的事实论证之上,“漂泊”作为成长的旅程与必经阶段而成为叙事的主要部分,但只有在汪中的漂泊终结于革命时他的漂泊才具有成长意义。“丧父”的汪中最终投身革命,在现代中国社会这一“克里斯玛式”的概念与话语系统中,通过汇入主流/父权性质的革命之中,而获得生命的归属感。茅盾的小说《虹》中主人公梅行素的漫游人生经历也被赋予了成长的意味。同样是在漫游中成长,只是因为成长主体的性别不同,起点由汪中的“复仇”替换为“逃婚”,女性气质的韦玉与鄙陋的柳遇春成为漫游成长中的梅行素人生历史上翻转的旧页,而梅行素的漫游欲望与其对男同事、对周遭世界的鄙弃同步而来,直到出川赴沪之后,梅行素才在革命与革命者梁刚夫那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魅惑力,产生了不可遏抑的献身冲动,终于在五卅运动中引领着游行罢工的队伍,充满了“意义”附体之后的生命力量的充盈感———革命成为梅行素生命漫游的终结点。《虹》反映的历史时代在小说《追求》之前,写作时间却在《追求》之后,但相隔亦不过二三年时间,却将其绝望意味的封闭的叙事空间扭转为成长意味的漫游的线性时间进程,显然后者更符合革命话语的规范性。革命话语影响力之外的“漫游”则往往与心灵的迷茫,生命的挣扎和失去意义的凭依等意味相关联,如果成长一定要与某种终极价值或主流文化认同,那么于此,漫游并不必然意味着成长。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由上海出发途经浙、赣、湘诸多县市,阅历风俗的同时亦领略同行知识者的心灵世界,如果把成长定义为对生活某种本质性的认知,这可以说也是一种成长,然而这种成长不像革命成长主体那样表现出对所处世界的超越与隔绝,而是与世界仍保留着某种同构性关系,最后方鸿渐又回到了上海,遭遇了家庭与事业的双重挫折之后,孤独地徘徊于寒风中的街头。一个循环的封闭式结构由此形成,成长于此没有意味着一劳永逸的安宁与平静,而是在对无意义的“循环”的既接受与又抗拒的悖性力中沉浮。如果说在《少年漂泊者》与《虹》中,“革命”作为终极价值解救了寻求意义的漫游者。那么,“在一定的循环永无止息地进行的基础上,我们只能期待不幸与幸运,即虚假的幸运和真正的不幸的一种盲目回旋,而不能期待永恒的天福,只能期待同一事物无休无止的重复,而不能期待任何新颖的,起解救作用的终极的东西。”———这是陷入循环叙事结构中的成长主体的宿命。
(二)
漫游与成长亦可于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中读解而出。《伍子胥》是作于1940年代抗战的动荡环境中的复仇故事,却通篇弥散着静穆的氛围。这种静穆不仅来自夜的赋予:“他白昼多半隐伏在草莽里,黄昏后,才寻索着星辰指给他的方向前进。秋夜,有时沉静得像湖秋水,有时动荡得像一片大海;夜里的行人,在这里边不住地前进,走来走去,总是一个景色。身体疲乏,精神却是宁静的,宁静得有如地下的流水。他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冬眠的生物,忘却了时间。”这种生命体验当然来自作者。《伍子胥》是与散文集《山水》同时期的作品,都产生于昆明市郊外林场的茅屋的静夜之中。自然山水的静穆之气,连同生命的孤独渺小感留在了作品中,形成了氤氲其间的静穆氛围。廓大静穆的宇宙中孤独的生命个体,其间的意蕴正如帕斯卡尔所谓:“这无穷的空间的永恒的静使我悚栗!”伍子胥是历史人物,却有一颗现代人的灵魂。小说中伍子胥从城父出亡始,以所经各地的遭遇构成小说的内容结构,共九个部分。虽然复仇的意愿指引着伍子胥出逃,却不能使其明晰脚下的路程。在洧滨、伍子胥未能与太子建达成复仇意志的同一,由此伍子胥想到:从这里燃不起复仇的火焰,他冒着最大的危险,辛辛苦苦到了郑国,想不到是这么一个结果。从而认定自己从城父到郑国的这段路程是白白地浪费了。正是路途的迷茫,歧路的纷呈,才使其旅程成为漫游,才使路途的选择与个体生命相关,因而伍子胥一路走来不仅形貌大变,也深切地感到自我生命的蜕变,就是在孤绝之境的昭关,黑夜中隐伏着的伍子胥深切地感到新的生命即将蜕皮而出。从复仇出发的伍子胥最终仍然决断以生命拥抱复仇,但却是在经历遭遇了林泽的楚狂、江上的渔夫与溧水的浣衣女带给他的“一个反省,一个停留,一个休息”之后,是有了如下判断之后的选择:“这些地方使他觉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关那样沉闷、荒凉,人间也不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样地卑污凶险,虽然廖若晨星,到底还是有可爱的人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着。”
如前文所述,《伍子胥》产生的时代背景使小说最后的“拥抱复仇”的决断成为对时代主流精神的认同,甚至可以对译为“坚决抗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人物伍子胥所承载的现代灵魂的漫游成为了获得时代“共名”的成长仪式。也许《伍子胥》中氤氲的宁谧静穆正与这种对时代精神的认同相关,正是这种认同,使伍子胥所承载的现代灵魂虽然漫游着却总有一种安宁气质伴随左右,而没有激烈的心灵的动荡、冲突甚至分裂。同时代的一位批评家就认为冯至“没有如巴尔扎克样把一个特定社会的风俗作一次有系统的介绍,也没有杜斯妥耶夫斯基那样,把那逃亡者的颤动的灵魂细细分析、重重锤炼;……那一夜白了头的故事该是杜斯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在这里却给诗人梦似的抒写冲淡了”,然而这份即使在漫游中,即使在忧患中,仍然持有的心灵的宁谧与玄思气质,才是最为独特的、最为强大的一种灵魂也未可知。《财主的儿女们》下部中的蒋纯祖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漫游至死未休,意义饥渴症与皈依权威话语的焦虑症似乎与漫游主体无关,而使漫游成为绝对的没有目标与目的地的漫游,最后终止的只能是肉体的生命,漫游仍然拒绝休止,从而使灵魂绝对的自由也绝对的孤独无依。“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胡风的批评中有对黑格尔“历史理性”、“历史必然性”似的“历史命运”之权威的尊崇,但他欣赏的是心灵与历史命运的对话与搏斗中显现出的心灵“火辣辣”的生机,而不是二者间完全同一显现出的心灵的贫乏或伪善。确实,蒋纯祖的漫游没有既定的轨迹、也没有被许以终极价值的允诺,是没有预约成长的漫游。终极价值的降临给叙事带来的是一种宁静而辉煌的光泽,在“意义”光辉的普照之下,痛苦挣扎的生命与灵魂获得了永恒的归宿感。拒绝皈依于某种价值的生命则始终左右奔突,崇敬灵魂的高贵亦正视地狱般的心灵罪恶。生与死、善与恶的倏忽降临与瞬间转换,远离了革命道义论之后的叙事涂上了肃穆而高贵的光泽,而这样的灵魂在革命话语观照之下难免被判定为歧路迷途的灵魂,依据功利主义价值观则是无用的灵魂。在现代文学中,通过漫游获得成长是革命话语君临叙事的结果,而未曾皈依革命话语的漫游则可能是绝望意味的循环,或是勇者无畏的也无止境的心灵探寻,或者说意味的是另一种成长:拒绝外在既定价值赋义,使成长与个体灵魂始终相系的成长。
作者:万杰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