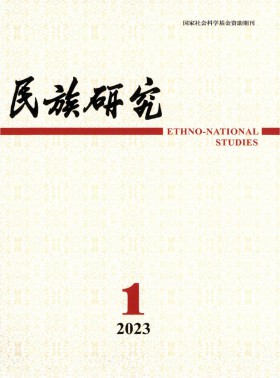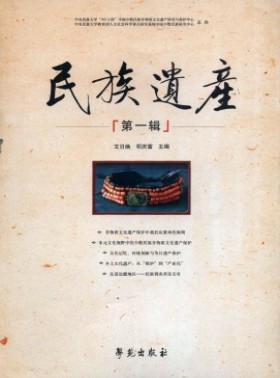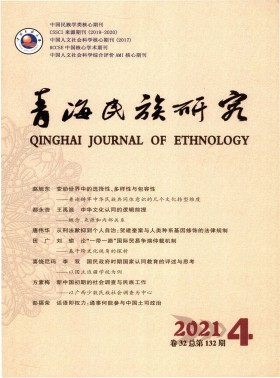一、企业民族文化责任
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经济利益之实,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业的真实写照。虽然单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之目的来开发民族旅游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却无疑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使民族文化在社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转瞬成为经济理性的工具,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深深地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这种伤害显然违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原则,即不伤害。“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准则可无条件普遍化。照此,伤害他人的身体和精神从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准则。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普遍化的准则,就等于允许别人去伤害他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不伤害伦理原则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而由人所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冲击和面临伤害时,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民族旅游企业对社区居民民族情感的伤害属于精神的伤害,虽然不像经济利益等物质层面的伤害那样显见,但这种伤害更深入,更具杀伤力。民族旅游企业到民族社区开发旅游项目,虽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企业至少应确保其自身的开发行为不会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伤害,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企业所谓民族文化责任便是欺世的空谈。保护总是包含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之意味,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重了强势群体的责任负担。在民族旅游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民族社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就凸显了强势对弱势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因为强势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更显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强势与弱势又总是相对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岂不也是弱势?所以,不伤害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群体、所有民族的。其实,强势与弱势本身可视为被一些所谓“睿智”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推论:民族之间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强势“应该”帮助和保护弱势,等等。照此推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汉文化在美国人的眼中同样也是需要保护。“正如我们很少听见少数民族对汉族说要保护好汉族的文化,但却可以听到美国一些学者在中国的讲坛上大发宏论说要‘保护好汉文化’一样,这和我们冠冕堂皇地对少数民族说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是同出一辙的。”如果按照“强-弱”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汉文化应欣然接受美国的保护,犹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应欣然接受汉族的保护一样。但显然,这样的“宏论”是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面前“强势”的汉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汉族深感“受伤”。如果“强-弱”的对比是一个事实的话,也应更多地被理解为或被看成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这一差距与文化无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并无强弱优劣之分,无法也无需做出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任何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应该是对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谓强势对弱势的保护,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业对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方面首先应明确的价值观念,因为那种以“强—弱”思维为模板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如不加以纠正,还将继续造成对所谓弱势的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民族情感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是应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首先应摒弃传统的所谓强势对弱势的居高临下般姿态的保护的误导性价值观念。这种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应有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潜在着对民族文化伤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摒弃这种误导性价值观念之后,民族旅游企业将会发现,其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实在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为它所保护的民族文化与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应受尊重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根据利益相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的文化保护责任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类:(1)直接对象: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是其传统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与所有者。(2)间接对象:人类社会。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由具有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负责,其伦理价值无疑远远超过因为保护民族文化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伦理价值不是用经济价值能够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被干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三、社区民族文化责任
如果说旅游企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保护的层面的话,那么,民族旅游社区所应该和必须承担的民族文化责任则除了保护之外,还有传承和发展。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意识是自内而外的,而非某种外部力量的强加和迫使。“旅游是能促使社区居民直接认识到自身文化价值的工具,能够增强社区内部的族群文化保护意识,这种由内而外的保护才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旅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起到激发和调动作用,不仅因为旅游可以使社区居民直观地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经济方面的工具价值,而且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保护民族文化犹如保护民族和族群的存在一样,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这种动力是不假外求的,是自然而然的,又是蕴藏着无尽的潜能的。民族旅游是以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的民族社区为基础和依托的,这也是民族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如果没有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吸引物,而仅靠景区静态的民族文化展示和讲解员背得滚瓜烂熟的民族文化解说词,很难想象这样的民族旅游地对旅游者有多大的吸引力。“从旅游供给的角度来看,文化传统是接待地发展旅游的基本财富,强调和维护本土文化的传统性实质上等于强调和维护接待地的旅游吸引力。”要想保持民族旅游地对旅游者的持久吸引力,就必须切实保护和维护民族旅游地社区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对其本民族成员更具有内在的恒久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以一种无形而无穷的力量将民族成员紧密地聚合统摄于一体,民族文化的历史越悠久,内容越丰富,表现形态越多样,在此基础上所开发的民族旅游就越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吸引力。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代代相传、世世沿袭的影响力甚至堪比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底蕴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来投资者断不会到民族社区开发民族旅游。民族社区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却有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虽然经济与文化是两种属性不同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不具有可比性,但民族旅游将二者奇妙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民族传统文化确实为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开发者带来了经济上看得见的“善”,从而打通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那层“阻隔”,也使民族社区居民更加珍惜和珍视自己祖祖辈辈用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并承继延续至今的民族文化,并将保护民族文化看成自己分内之事,把这份责任看成是当然之责。社区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是伴随着一种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的,他们将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视为神圣的职责。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和日益深入的发展,由于景区本身容纳和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规模和能力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区的一部分年轻人就开始走出社区,外出打工或另谋职业,这无疑给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危机。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不是因为发展民族旅游,也不是来自市场经济,而是来自民族自身。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自身的传承,是民族前辈往下的传授,民族后辈向上的继承。”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是民族自身的危机,如果因为民族旅游的开发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而造成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只能说明该民族文化本来就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民族旅游和市场经济这样的外部因素就可能自行消亡。民族文化之传承是持续的接力,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之上传下承的过程,绝不会因为民族旅游的不速而至或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动而嘎然中断。民族社区既承担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又肩负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在民族旅游中,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在与异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往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既得到了传承,也得到了发展。“事实上,民族文化是一种持续建构,民族文化并非某种自我规定,它取决于与异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发生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现代语境下,任何文化为了更新自己或影响其他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特质———民族性的去除,而是表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导致的一些自身东西的失去,可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或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新陈代谢的自然结果。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常态。对于民族文化弥足珍贵的东西,就是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更何况在现代语境下,保守封闭已无可能。保守封闭状态下的对民族文化的“不舍”不但不能有所得,而且还会失去更多。在民族旅游这一特定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场域中,民族社区承担着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责任。民族社区与民族文化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社区民族文化责任必然是当仁不让的和完全“强制”的。企业一般不会对社区提出这种强烈的要求,而政府即使提出一些要求,通常也是以倡导性的表述或“软约束”的形式出现。因此,这是民族社区的一种自我强制和自我设定的义务,每个社区居民都成为自我设定的义务主体。虽然在民族旅游的开发与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个社区居民所参与的具体工作和所面对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从而产生民族文化责任实践中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可以肯定的是,社区民族文化责任的实践效果绝非民族旅游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比拟。
作者:冯庆旭 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