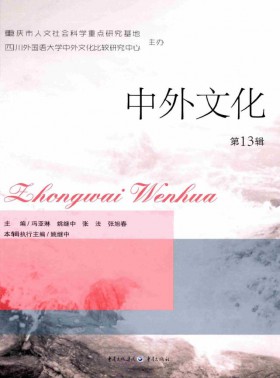一、作为政治策略的一种“文化”角色
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为了建立民众对于新兴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同,国民政府尝试以“中华文化复兴”为核心理念,在本土范围内强制推行符合“中华意识”的文艺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压制与此理念相对立的地方文化,如地方方言、民间技艺、宗教活动、乡土文学等等,企图消融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软性的文化控制策略在凝聚社会共识、统合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工商社会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后,台湾不得不开始面对“乡村人口逐渐外移,造成城乡极度不均衡,城市就业人口增加,缺乏对社区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开始动摇”的现实。同时,“原本凝聚乡里庄头的地方常民文化,也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经、科技优势而逐渐萎缩。工业化、标准化的取向,使得地方的独特性慢慢消失,传统与文化艺术不再能突显社群或小区向心力”。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当局高度控制的中央集权和威权统治,一连串的空间改造建设导致实质的生活空间、生活质量及自然生态深受威胁,长期打压乡土文学及本土文化形成反弹效应,党外运动逐渐萌芽。尤其在1987年后,言论自由得到官方认可,民间政治力量开始逐步释放:“社会运动越演越烈,小区运动、草根自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又兴起小区自主风潮,要求地域自主的呼声升高,寻求文化认同之趋势更成为热潮。”在此现实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出于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始,台湾方面开始重视地方建设,并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正如美国学者沙伦•祖金(SharonZukin)所言:“文化在都市资本生产与地方认同感的结合下,具备积极的经济作用,使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成为都市复兴(urbanre-vitalization)的重要策略。”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不仅适应于都市,对于地方性环境而言亦如此。由此,“文化”开始作为一个政策议题进入研究视野。
二、“地方文化产业”:经济效能与身份认同建构
地方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地方”,即强调由地方历史记忆、文化特质、空间结构、人口属性等“内发性”资源所衍生而出的产业模式,具有强烈的地方依存性(Localdependency)与地域源生性等。地方文化产业以“地方意象”、“特色”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筹码,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产、乡土文化特产、民俗文化活动、地方自然休闲景观、地方创新文化活动、地方文化设施等。从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实施的现实效果来看,基于地方“内发性”的文化产业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在社会建设层面,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推动了地方文化硬件设施建设,提升了地方经济发展效益,而且还吸引了地方外流居民、创意人才以及外地资本等。其次,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的地域性凸显了“我”与“他者”的差异。在差异的区分和比照过程中,呼唤了民众自我身份的认同,有效地增强了民众的归属感,调动了民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影响日趋严重的当下看来,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已成为了台湾应对全球符码流动与文化殖民的重要利器。
三、台湾经验: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逻辑
“一般认为,某一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是政府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策略性产物。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现存正式制度、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社会资源以应对新生挑战的同时,也在试图改变或再生产社会结构。”因此,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紧密相联,其演变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变迁脉络以及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挑战。通过政策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可大致总结为三个阶段性特征:“文建会”的成立与文化建设的转向;“社造”运动与地方文化的全面发掘;全民动员与行政配合机制的建立。
(一)“文建会”的成立与文化建设的转向
如上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同时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国民党当局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1977年,“文化发展”首次作为政策条目在“十二项建设”计划中被单独提出,内容为:“建立每一县市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台湾“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综合发展计划》《加强文化及娱乐活动文案》《推行文艺教育活动实施文案》《修订社会教育法》等政策条例推动台湾文化建设。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台湾当局开始将建设的重心从交通、农业、重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渐渐转向本土文化建设。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力度,台湾于1981年将文化管理部门独立而出,成立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掌管统筹规划及协调、推动、考评有关文化建设事项与充裕国民精神生活”。其后,“文建会”牵头组建了“各地文化中心访视小组”,实地考察各县市文化资源,以制定具体政策辅助县市进行特色文化发展规划,并于1987年陆续颁布实施《加强文化建设方案》《县市综合发展计划实施要点》,明确目标要重新发掘各县市文化中心的地方特色,并结合地方传统工艺、人文特色以及特殊地理、历史发展背景成立县市文化中心特色馆。1989年,台湾当局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建设四大方案》以及此方案的修改版《“国家”建设六年计划》,其中包含文化建设文案共分25项计划提案,细分为157项措施,成为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计划,总预算高达200多亿元。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台湾一系列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深入发掘了全省范围内的特色文化,初步实现了地方文化的产业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各县市的文化创意人才,在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不能被忽视的是,这个时期台湾文化政策主要围绕台湾领导者的意志,即领导团体利用其掌控的行政权力与经济资源在各地进行地方文化硬件设施建设,以期实现本土文化振兴并建构民众的文化认同。显然,这种“自上而下”依赖中央经济补助、缺乏民众参与的文化建设计划忽视了地方文化特色的差异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众自主性和积极性,难以获得民众支持,更谈不上建构文化认同。比如,文化建设文案中提出的“文化园区”保存模式“将文物及活动自其所存的社会脉络中分开,使得文化成为失去生命力的标本,同时由政府出资经营观光导向的园区,也因为经营缺乏弹性,无法随时顺应社会需求进行调整,终将成为政府部门的负担。”这显然违背了地方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诉求。因此,如何凸显台湾地方文化的特色和差异性,如何调动民众自主性和积极性,并建构民众的地方认同,成为后续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
(二)“社造”运动与地方文化的全面发掘
20世纪90年代前,台湾“文建会”的文化政策仍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理念,但初步呈现出对各县市地方文化特色保存的重视。这种趋势在1993年申学庸担任“文建会主委”后开始日趋明显。申学庸第一次在“行政院长”莅会巡视时提出了未来几年台湾文化建设的几个重点方向,其中针对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包括:“1.文艺季的转型,以‘亲、土亲、文化亲’为主题,由各县市文化中心主办,组合成全国性的活动系列;2.地方文化自治化的推动,以文化中心为主体,扮演地方性的‘文建会’角色,统合地方文化行政体系,负责策划、协调和融合地方文化资源;3.建立文化行政工作者的地位,培养文化行政人员的能力与经验,做为推动地方文化工作的主力”。报告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定期举办文艺季活动以发掘和强化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达成“文化地方自治化”的目的。至此,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念形成雏形,并成为了影响台湾后续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核心原则。1994年,“文建会”将这种理念具体化为可行政策,产生了《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社区文化软硬体设施》十二项计划。其重要意义在于将过去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规划权开始下放至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组织,同时,将原来相对抽象的建设计划转化为地方社会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看,重新发掘“在地性”文化不仅可以挽救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同时,缓解台湾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正如陈其南所言:地方文化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透过改造地方社会来培育文化艺术发展基盘,另一方面透过文化艺术发展来达到从地方社会再造达到整体社会国家再造的目的”。由于“十二项建设计划”的实践理念受到了当时台湾领导人的肯定,同年,以陈其南为代表的“文建会”智囊团提出并掀起了一场名为“社区总体营造”的全民性运动,将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推向了高潮。“社区总体营造”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活动发展计划;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辅导县市主题展示馆之设立及文物馆藏充实计划;辅助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社区总体营造”是一场“通过强调社区文化,对台湾寻根文化思潮与政治对抗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的行动,主旨在于建构台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领导集体与民众之间的共识”,其本质是通过文化的手段“重新营造一个社区社会和社会人”。“社区总体营造”方案充分激发了民众的文化想象、权利认知与自发性创造能力,挖掘了曾处于受忽视或停滞状态的边缘文化,将台湾地方文化的振兴及产业化带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从政策制定的初衷及其现实效果来看,“社区总体营造”与“十二项计划”的核心差异在于,前者更侧重对“人心”的改造,着重于增加地方民众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感和自主性,建构民众对台湾的“共同体”意识,其最终目标为引导民众“从街头走入小区;从激愤走向长期经营;从议题与事件的抗争走向选民价值观的普遍再造”。因此,“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也被描述为“深耕地方基层文化的‘宁静革命’”。其后,1999年“文建会”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基础之上再提出《振兴地方文化产业、活化小区产业生命力》计划,将地方文化产业单独列为政策对象明确标识,旨在“辅助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文化产业振兴工作、策办地方文化产业振兴与理论与实务研习工作、办理地方文化产业振兴与经验交流座谈会工作”,同时,政策创新性提出“一乡一物一特产,一村一品一艺文”的发展目标。2000年,“文建会”再次细化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方式,在《文化产业之发展与振兴计划》中增加“办理产业文化之旅观摩活动、编印地方文化产业特色简介、实务研讨、经验交流以及成果展示活动等等”。“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以及后续补充政策不断将产业建设措施细化,以全面发掘台湾“在地性”文化产业,同时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与经验的可复制性。不过,此阶段的文化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计划目标重叠、资源浪费,比如“在莺歌地区文化产业建设过程中,经济部商业司的商圈更新计划、县政府的陶瓷博物馆兴建、内政部营建署的城乡风貌改造计划等”在建设目标上多有交叉之处,极易造成责任不清、资源浪费等现象;其次,还表现在文化建设资源过于分散、硬件设施建设缺乏软体配套,比如台湾学者洪菁佩在对台湾地方文化艺术节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资源有限情形下,为了建立地方艺文特色,文化资源往往必须分配到少数几个文化项目上,也因此,其他的艺文活动需求相对被忽略或排挤。”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缺乏“政府”内部跨部门、“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之间跨层级的协调配合机制,而这也成为了下一阶段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着力解决的核心所在。
(三)全民动员与行政配合机制的建立
21世纪初台湾加入世贸组织,这意味着台湾将迎来信息符码的加速流动与传统产业发展竞争的升级。对于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可能是新一轮的文化殖民化与同质化威胁。为了有效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文建会”在总结过去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教训后,于2002年及时出台了《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划》,其中最后一项即为《新故乡社区营造》,内容包括:原住民新部落运动、文化资源创新活用、乡村社区振兴运动、内发型地方产业活化、健康社区福祉营造、新客家运动。随后分别于2003年、2005年出台相应的补充政策《社区营造条例草案》《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与之前的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相比,《新故乡社区营造》及其补充政策的意义在于尝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跨部门与跨层级的行政配合机制,着力解决“社造”阶段目标重叠、资源分散甚至浪费等问题。其基本理念是:“政府部门不主动订定计划內容、选定执行对象及执行方式,而只是提示计划鼓励方向与重要价值,执行上完全开放给社区组织提案,进而视其提案之创造性与可行性来决定经费补助的规模。”同时,“文建会”成立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推动办公室”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资源调配问题。其次,“文建会”还制定了包括“补助型计划、分区专业辅导机制、委托专案管理中心、培训计划、特定主题委托研发”五项政策工具,试图在民间提案内容、行政配合机制、资源统合、人才培育等方面建构起分工合理、沟通顺畅的合作体系。更引人注意的是,相比之前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只注重培养艺文人才,《新故乡社区营造》开始关注吸纳更多的居民群体参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并首次提出培养青少年与妇女两个群体,内容包括:《活化乡村青年组织与活动》,倡导通过“做中学”教育理念,鼓励青少年参与“自主性筹组运动型社团,休闲娱乐型社团,资讯技能型社团,民俗艺阵社团,传统工艺社团,传统音乐社团”,达到培养“全方位的农村青少年”的目的。政策鼓励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课程,参加文化创意的实践等措施,从小培养青少年文化创意的观念和意识,为未来的文化创意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变迁脉络概括为三个重要转向:
1.从“政府”主导转向地方“自治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十二项计划”伊始,台湾开始改善传统式由政府决策、缺乏民众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逐步下放文化规划与政策制定权,主动吸纳地方相关文化部门与民间力量加入到地方文化产业建设中。由此,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越来越贴近地方文化发展的实际,初步呈现出地方文化“自治化”的趋势。从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文化认同以巩固合法性的必要过程,同时也有效地弱化了民众的政治抗争行动;而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确实提高了民众对地方文化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并培养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
2.从“各自为政”转向建立行政配合机制。
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需依赖多个部门的互助协调机制,如地方政府部门、经济产业推动机构、地方文化教育与研究部门、媒体传播机构、地方社群力量等等,各部门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驱动产业的发展,形成“整合作用大于个别之和”的合作效应,否则很可能导致地方资源的浪费以及政策执行的困难。以《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为例,如果要顺利实施,就必须“内政部”、“农委会”、“文建会”、“教育部”、“客委会”、“原民会”、“环保署”等多个部门协调各自内部利益分配,并建立部门间互相配合甚至互相妥协。不仅如此,政府部门与地方居民的跨层级合作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从“各自为政”走向社会整体配合机制的建立是台湾“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3.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全民动员。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主要以推动地方文化硬件设施为主,旨在为地方文化展演提供平台。1994年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过程中,“文建会”开始意识到创意人才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政策中对创意人才群体的重视与培养。直到2008年《新故乡营造计划》才真正意识到广泛动员各界居民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并不是一个自我维持、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其要不断获得资讯、智慧、技术、资金以及自然资源等支持,避免过多地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而通过智慧等资源等不断投入与优化整合,推动文化产业,并实现再扩大生产。”这里的“智慧资源”不仅仅包括创意人才,还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普及产业发展成果的民众等等。其次,从政策的政治指向来看,只有将尽可能多的民众有效动员起来,才可能为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及产业建设寻找合法性,同时“将底层的民主力量从议题抗争引向生活价值观的再造,以最小的代价成功完成社会的认同再建构”。这是台湾文化产业政策理念与实践层面的一次重要转变。
五、结语
总之,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不仅注重经济效益,还同时注重“地方性”在民间所发挥的整合社会、凝聚民心的特殊作用。通过政策的不断完善,地方文化产业从最初的政治策略变为全民共享的产业,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了宏观政策与民间力量的高度融合,避免了为实行政策而发展产业的尴尬局面,这为台湾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林颖 吴鼎铭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