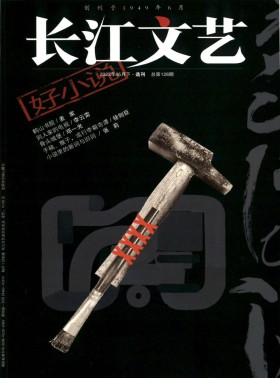文艺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历来为创作者和文艺理论家们所分外关注。作为在西方文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对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其理论成果虽历经千年依然值得珍视。本文拟采取比较诗学的视角,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对创作灵感问题的探析,以今时今日之视角对柏拉图的“灵感说”做出新的阐释。 一.《文艺对话集》中的“灵感说”理论思想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伊安篇》集中阐释了其“灵感说”思想。伊安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个职业诵诗人,精于朗诵《荷马史诗》即《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并在文艺竞赛中屡获成功。对话中苏格拉底和他讨论的主题是“诗歌创作究竟是凭专门技艺知识还是凭灵感”。柏拉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柏拉图认为,诗人创作并非凭借技艺而是依赖于灵感,依赖于神灵,神灵附体产生的迷狂状态激发了诗人创作时的巨大灵感,简言之———“诗灵神授”。柏拉图做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如果诗人是凭借他的技艺来创作,那么他就能够遇到任何题目都发挥自如,产生佳作,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是一个著例,可以证明我的话。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谢神歌》,那是人人歌唱的,此外就不曾写过什么值得记忆的作品。”另一方面,柏拉图从创作者和包括伊安在内的诵诗人的实际创作状态出发,创作过程中他们往往神智不清,失去自主,完全沉浸于艺术的海洋中,连聆听的观众也如痴如醉。对此柏拉图以磁石作喻,“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身上,由那些诗神凭附着”,“诗人是最初环,旁人都悬在这上面”。这种解释在后来影响深远,直到近代托尔斯泰宣扬他的“感染说”时,仍能见出其中所体现的柏拉图“磁石”比喻的理论思想。对于“灵感说”柏拉图是坚定不移的,在《文艺对话集》的《斐德若篇》当中,柏拉图再次重申了他诗神附体产生灵感进而流露于诗歌这一观点,并且说“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将文艺创作完全看做是神灵和灵感的产物。在与斐德若对话过程中,他甚至会突然停下来向对方发问,“我觉得有神灵凭附着我,你听我诵读时是否也有这样感觉”?在《斐德若篇》末尾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他仍然认为“在我们头上的那些歌蝉,给了我的灵感。因为我知道自己,至少我是不懂修辞术的”。可以说,柏拉图对“诗灵神授”的“灵感说”是没有任何怀疑的,这一思想也是柏拉图许多其他重要理论思想的基石,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二.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灵感说”之比较 应当说,对创作灵感的重视在中西文论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且中国古代谈到灵感问题时也往往不乏神秘色彩。成语“江郎才尽”典出《南史•江淹传》,传说江淹献出了一支五色神笔后再难写出佳句。钟嵘《诗品》在中品之中谈到江淹的诗歌成就时同样论及此说,并明确称是郭璞在梦中拿去了本属于他的五色笔,尔后江淹文采即大不如前。“文通残锦”这个成语也是说江淹梦见张协要他归还了一匹五色锦缎,从此再难有佳作。再如曹植做《洛神赋》,传说是夜泊舟中梦见甄妃凌空而来,心有所动,从而援笔作赋。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一诗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浑然天成,余韵悠然,史传为“鬼谣”,乃是钱起于江上舟中听空中神鬼所吟,实质上,说得仍然是徒然其来的灵感现象,类似故事在涉及我国古代诗文名篇名句时屡见不鲜。古人将佳作绝句归功于神灵启示或是梦中得句,同西方柏拉图的“诗灵神授”在本质上来说是并无二义的,都反映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灵感现象的惊异和赞叹,对突如其来的神思妙笔的惶惑与欣喜。但是就具体文论思想而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对灵感的思考与柏拉图还是有所不同。陆机在文赋中谈到灵感的“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时,也注意到了其“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的一面,从动、静两方面来看待灵感。同样地,宋代文豪苏轼也有“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的观点。对“空”、“虚”、“静”的追求,在虚静、灵明的精神状态中去捕捉灵感,“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种文学创作思想应该说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同柏拉图所一再强调的那种如癫如狂的“迷狂”状态有着很大不同。柏拉图看到巫师们的舞蹈、看到抒情诗人作诗以及诵诗人激情澎湃的朗诵,“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在哀怜之处热泪奔涌、难以自持,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从这种经验事实出发,柏拉图的“灵感”与“迷狂”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更强调的是一种激情的作用,一种创作者在主观情感特别充沛、饱满之际的兴奋状态。但是中国古代文人由于长期受儒道两家思想文化的教化与浸染,一方面接受的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方面汲取的是老、庄那种悠游自然、无欲无求的本真思想,不可能像西方诗人、剧作那样或高歌或恸哭,在各种祭典或竞赛上恣意张扬。因此,早在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已经在其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中旗帜鲜明地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要求创作主体在创作时排除内心的杂念和欲求,返归到一种清虚空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去吟诗作文,才能与自然万物取得细微的感应,从而付诸诗篇,成就璀璨文章。而再返观柏拉图的论述,他所一再提到的“酒神的狂欢”、“酒神的信徒”、“酒神凭附”无一不是强调“动”的一面。希腊人所崇奉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是葡萄酒之神,神话中传说他惯以甘甜的葡萄酒醉人,向世间散播欢乐和慈爱,因此酒神的凭附所带来的灵感当然是飞动的、迷狂的,和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思有着很大不同。可以说,对创作灵感那种突发性、神秘性的感受,中西方是相同的。但是与柏拉图的“迷狂”相比,中国古代文人十分看重创作中“虚静”的心态,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其自身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浸染影响的结果。#p#分页标题#e# 三.对“灵感”现象的科学认识 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思维求之不得又往往不期而遇,令古往今来的创作者们心醉神迷。孙文宪教授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灵感思维的特点概括为“偶发性、短暂性、亢奋型、创造性”四个方面,应该说,对灵感思维之特质的认识堪称全面。“偶发性”强调的是灵感到来的不可预料,这在中西方文论家那里是共识。“短暂性”要求作家在灵感到来是必须敏锐地将其抓住,辅助创作实践,所谓“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即是强调对灵感的珍视。关于“亢奋型”,并非说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强调的“虚静”是错误的。灵感在到来的时候,都是以一种亢奋活跃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文论家所强调的“虚静”,是捕捉灵感的一种手段,是在灵感到来之前奠定的心灵土壤,是作家为灵感所作的内心修为,这与柏拉图所强调的“迷狂”并不矛盾。只不过柏拉图更多的强调的是灵感到来之际的状态,而中国古代文论家着眼的是灵感到来之前的作家准备。 近代科学的发展早已让柏拉图的“诗灵神授”难以立足。根据心理科学的阐释,灵感生成于潜意识的酝酿,当艺术创造者的意识松懈时酝酿的成果往往猛然涌现,伴随着丰富的情感和想象产生出创作者始料未及的艺术成果。灵感并不神秘,它的得来也绝非“神授”,一如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中所说“灵感也要有预备”。中国古代文论讲“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但同时也强调作家个人修炼的重要性,袁枚《随园诗话》云“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可以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论断。与柏拉图相比,这种务实的创作思想显然更为辩证。 总之,柏拉图对灵感与迷狂的思考与表述,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智慧成果,也开启了后世对灵感问题挖掘和探索的大门。与中国古代文论不同,柏拉图更看重的是“灵感”飞腾动态的一面。而究其实质来说,灵感不过是潜意识中酝酿成果在成熟时期的自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