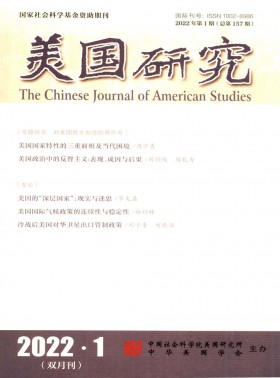摹仿强调镜像式的再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戏仿是差异性的摹仿,它借用、修改和超越原物,追求个性风格,它的批判性,创新性体现了现代主义精神;伪戏仿摈弃了批判思维,是中性的,自恋式的文本游戏,体现了后现代对形式和语言进行试验的嬉戏态度。摹仿、戏仿、伪戏仿三种美学策略见证了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非裔美国文学在20世纪前主要是对白人文学范式镜像似的摹仿。到了20世纪,它开始通过戏仿建构以“‘重新比喻表达法’或是‘重复及差异’”①为核心的“黑人性”,力图发展具有黑人文化特性的黑人文学。进入后现代,非裔美国文学又加入文本游戏的浪潮,呈现出破碎、片段、不确定性等特征。自此,严肃与创新的戏仿被体现了后现代能指嬉戏精神的“伪戏仿”消解。由此可见,摹仿、戏仿和伪戏仿不仅分别体现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本质,也见证了非裔美国文学从稚嫩到成熟,从寄生到自主的发展历程。 一摹仿、戏仿、伪戏仿三种创作范式 文学艺术的“摹仿”说流行于古希腊早期,那时人们用摹仿一词来界定艺术的本质。赫拉克利特提出“艺术摹仿自然”,“以便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②柏拉图以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式论”对“摹仿论”进行改造,认为摹仿“就像镜子照物一样,只是客观事物的外貌复现,不能模仿事物的实体(本质)”。因此,“摹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③亚里斯多德强调艺术的创造,反对消极的摹写,他认为艺术应该是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这种方法直接导出了“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的论点④。这个观点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他虽然称艺术是一种模仿,但同时“艺术必然是创造”。后来,贺拉斯进一步揭示了创作主体的重要性:“艺术摹仿生活是通过作家主体判断的模仿”。早期围绕摹仿的讨论已可窥见戏仿的萌芽。“戏仿”又名“滑稽模仿”、“戏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598年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的《牛津英语辞典》:“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随后,戏仿的概念便在不断地“旅行”中。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依•巴赫金把戏仿和民间文学及狂欢化联系在一起,从写作技巧方面对戏仿做了详细的定义:“戏仿时……作者采用别人的语言……他在引用的这个语言中加入了与原语言完全不同的意图。这个新的意图一旦入住,就会和原语言发生冲突,迫使它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 巴赫金还指出了戏仿的几种变体:“可以戏仿文体,或者是具有社会典型性或个体特性的观察,思考和言说方式。戏仿的程度也有变化:可以戏仿话语的表层形式,也可以戏仿其它话语行为的最深层原则。”⑤异言之,戏仿包含了来自源语言和添加在源语言中的新意图两者之间的相互冲突的意义,既有不同层面的戏仿,也有不同程度的戏仿。从时空叙事策略的角度分析,使用戏仿手法的作品有“母本”和“修改文本”双重文本空间,两者在冲突和融合中形成了艺术张力,形成了带有多声部的复调叙述,生成“共时性”的空间模式。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对巴赫金的戏仿改造和挪用,从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赋予“戏仿”的政治功能。巴巴指出具有后殖民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蕴含着“几乎是同样但又不完全是同样”⑥模仿策略。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模拟”,显示“差异的再现”,⑦帮助生成了一套“模拟两可”和“混杂”的话语,这个话语既对原体模仿,又有意与之不同,它所产生的讽刺性效果削弱并破坏了西方思维和写作方式的整体性。因此,这种模仿成为边缘话语如何从内部向中心主流话语实施压迫,进而颠覆其权威的手段。戏仿在“旅行”中产生了变异,但它内含的创新性和批判性始终未变,其固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体现了现代主义事业中仍然存在的人文关怀理想和自我批判性。 贺拉斯在《诗艺》一开头就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看见这幅画能不捧腹大笑么?”⑧如果贺拉斯能活到今日,读着后现代小说,或许他会笑死,因为他视为胡拼乱凑的,不伦不类的“不适合”诗的东西已成为后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充分体现了后现论家博德里拉提出的“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的观点⑨。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把这种游戏笔墨的大杂烩定义为后现代主义戏仿。他认为,“戏仿”有“价值的增删”,“背后隐藏着别的用心”,有“讥讽原作的冲动”,但后现代戏仿不再追问价值意义,发展成一种空洞的戏仿,是一种“没有隐秘的动机,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嘲笑,没有那种仍然潜在的感觉”,“绝不多作价值评判”的中性手法,是失去个人风格和历史意识的“拼凑”,是“根本破碎化的结果”,是“以前的戏仿失去其全部功能后所剩下的一切”,因此,这是“伪戏仿”或“空白戏仿”⑩。詹姆逊中性的“伪戏仿”遭到后现论家琳达•哈琴的质疑。哈琴认为后现代戏仿是一种悖谬的、具有“双重赋码”政治性、颠覆性极强的艺术形式。???早期哈琴把戏仿宽泛地界定为“反讽式的引用、拼凑、挪用或互文性”等。后来,她把戏仿修正为“带有批判距离的重复,它能从相似性的核心表现反讽性的差异”,“批评”和“反讽”等字眼凸现了后现代戏仿的“政治性”。 黑人文学理论家亨利•路易丝•盖茨在研究非裔美国文学史时指出“黑人文学表意方式犹如戏仿和伪戏仿”。黑人作家对前文本进行“有动机的表意”与“无动机的表意”。戏仿内含对一个文学传统内部的严厉的批判,属于有动机的表意;伪戏仿为无动机的表意。???综上所述,摹仿强调“相似”、“再现”的现实主义原则,“戏仿”强调差异,凸显个人风格,它内含的批判性使其具有现代主义气质。“后现代的戏仿”不管思想上有无政治性,仅从文学形式上来说都充斥着后现代主义彰显的艺术“性感”新感受,沉浸在形式和风格的愉悦中,力图远离现代主义以追求以内容、意义和次序为核心的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二非裔美国文学发展的美学策略 (一)非裔美国文学的美学策略:摹仿。美国著名黑人学者贝尔教授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说道:“拿一半心思是为了准备给白人看,我知道另一半才是为了我。”???这一语道破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双重意识,双重眼光和社会化的矛盾心理。双重意识是指非裔美国人两个种族和两种文化身份;社会化的矛盾心理指美国黑人在种族融合还是分离问题上摇摆不定;双重眼光指的是对人生欲哭偏笑的视角。这些双重性一方面表明了白人文化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显示了美国黑人文学的边缘性和对主流文学的矛盾心理,这些构成了摹仿和戏仿的心理和社会基础。黑人女作家佐拉•赫斯顿曾说:“黑人在整体上以摹仿闻名……摹仿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摹仿是20世纪前非裔美国文学艺术的主要美学策略。但这种策略“并不出现在真空之中。他们是特定历史状况的产物。……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对当时的黑人文学而言,只有通过白人的认可才能成为艺术。黑人作家与白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张无形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无形中约定:为了更好地监控黑人,黑人必须忘记自己的过去,必须割断与传统文化的纽带,不能有任何动摇既定规范的举动。这样的规定决定了黑人文学在当时无法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的美国黑人作家同时只有放弃创新的意识和勇气,做一只擅长机械模仿白人文学艺术的“鹦鹉”。摹仿尤其体现在19世纪中叶最为流行的非裔美国文学形式———奴隶叙述中。1789年奥罗的•依奎奥诺(OlaudahEquiano)出版的奴隶叙述作品《有关奥罗的•依奎奥诺的生活的有趣记录》成为19世纪奴隶叙述的原型,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弗•道格拉斯,哈里特•雅各布斯,威廉•威尔士•布朗等人的创作。该书采用两个声音来叙述先前无知的和后来成熟的依奎奥诺,这种双声性叙事手段后来被广泛的直接的挪用在奴隶叙述中。第一位非裔美国小说家威廉•W•布朗在《克洛特尔》中引用的典故,引语和结尾也被认为是白人作家风格的“嫁接”。缺乏创新使得这些黑人作家的写作风格单一,写作内容相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劳伦斯•顿巴的黑人方言散文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早在1887年琼•H•斯麦斯(JohnHSmythe)就呼吁:“如果我们有错,那就是我们总是在模仿其他人……我们要努力让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模仿其他民族,只能用自己在文学、宗教、商业和社交方面的独特方式来实现。”顿巴在1899年的一次采访中无可奈何地说道:“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像白人那样写作。我并非说模仿,但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杜波伊斯认为20世纪前的黑人“由他人领导与支配”。1934年6月由他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危机》杂志无不担忧地指出了黑人近两个世纪缺乏创新的状况:“在这个令人沮丧和失望的时期……不要再把我们的原创性淹没在拙劣地模仿白人之中了。”???这些前瞻性鼓动性的言辞预示着即将而来的戏仿。 (二)非裔美国文学发展的美学策略:戏仿。盖茨曾指出:“我们的文学传统之所以存在,恰恰就是这些可图绘的文学形式之间的互文关系或表意关系”。互文实现的主要手法是戏仿。黑人文学的戏仿客体即包括白人文学也包括黑人文学自身,同时又存在对自我作品的指涉。戏仿在各个层面展开:主题,文字,形式,作家,内文本关系等等,戏仿的形式既有“有动机的”,也有“无动机的”。黑人文学的意义由此更趋丰富和丰满,更具艺术性。非裔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身份的寻求与探索,不同的作家针对这个问题阐明观点。比如,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暗示了“以暴制暴”的身份策略,凸显了身份策略中的政治性;黑人文学之父的拉尔夫•艾利森的《无形人》则提倡在黑白文化的融合中寻求身份,并将艺术性置于政治性之上;托妮•莫里森通过《所罗门之歌》表明,黑人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在差异中求生存才是可行的身份策略。???黑人先锋派作家珀斯沃•艾瓦瑞特(PercivalEverett)对艾里森的戏仿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形式和主题思想。艾瓦瑞特的《擦掉》(Erasure,2002)中的主人公芒珂•艾里森这个名字取自现代先锋爵士乐音乐家穗罗尼尔丝•芒珂和拉尔夫•艾里森,表明了作者对拉尔夫•艾里森的敬意。《无形人》中最重要的主题成分“无形”在《擦掉》中得以重现。两位主人公都不被社会看见,这种“无形”既有外界的强加,也有自我的意愿。芒珂•艾里森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遭拒,他们无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最终他“擦掉”自我,选择了“无形”。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无形人》的主人公是因为“黑”而不被看见,而《擦掉》的主人公是因为还“不够黑”而被忽视。除了主题的戏仿,还有内容和谋篇布局层面的戏仿。克拉伦斯•梅杰的小说《不》对艾利森的《无形人》进行了戏仿。尤其体现在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最终醒悟。《无形人》中的主人公最终意识到,“必须出来,必须露面……我得到地面上来,以我的千姿百态来奏乐跳舞……我正在褪去旧皮,准备把它留在洞里……因为,说不定即使一个无形人也可以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不》的主人公在小说开篇就与之形成回应:“我原来未意识到,我确实一直在努力逃出我出生并成长在其中的某种惩罚制度。但是,回顾过去,我的确认识到,我生活中的行为仅仅表明了我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道德事件中的身份而已。”最终,主人公意识到“必须赋予生活意义,而且生活必须包含勇气。同时,我与生活的浅薄争辩,同我自己争辩,同生命争辩。”???两者最终的醒悟是相似的,只是《无形人》中的主人公在最后还只是“正在褪去旧皮”,对将来还只是一种“说不定”的困惑,而《不》中的主人公则显得自信而更有勇气,并明确了“必须”同生活、同自己、同生命抗争的具体方案。美国黑人作家在相互戏仿的同时将白人文学范式纳入自己的互文空间。比如,莫里森的《柏油娃》以伊甸园神话作为隐喻模式,但又对之进行了修正。昔日纯美的伊甸园在男主角森———这里是撒旦的替身———的到来后“堕落”了,但堕落后的伊甸园反而让读者意识到了这个伊甸园的虚假和罪恶,从而告诫人们,伊甸园并不存在,在这纷扰的世界中,并没有什么乐园可以寻求。#p#分页标题#e# (三)非裔美国文学发展的美学策略:伪戏仿。伪戏仿策略同样被黑人作家们容纳吸收。艾里森的代表作《无形人》糅合各种文学体裁,比如书信、说教、论辩、歌曲、政治演讲、梦想等,使其叙事呈现破碎、拼凑等后现代文学的特点。???莫里森的部分作品的伪戏仿特征更明显。比如,《宠儿》进一步颠覆了体裁的界限,走向了无体裁的写作,合并了历史与虚构、魔幻与现实的种类混杂。黑人作家伊什梅尔•里德被詹姆逊视为最具有后现代性的作家之一。盖茨曾如此评价里德:“里德提倡的是美学游戏:关于传统的游戏,对传统的游戏,对文本不确定性本身的嬉戏。”???这句话充分肯定了里德反美学、反艺术、反文化的后现代游戏精神。里德对传统的小说题材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他的小说就是历史与虚构,神话与想象,黑人土语与学究味十足的标准英语的大杂烩。《芒博琼博》(MumbleJumble)是里德的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派反侦探小说。这部小说意义不确定性,宛如一本关于符号的手册,一部关于能指的教科书,充满了取自不同文本形式的拼贴。比如他将图片、相片、脚注、字典条目,互文引用,信手拈来的符号和招贴等融合一体,练就他的所谓“文学秋葵花汤”???:即把性质不同,毫不相干的东西并置在一起,让它们产生某种整体感。正是这种整体感促使一些学者拒绝把里德的后现代戏仿归为无目的的语言游戏,他们坚持认为,里德作品蕴含的政治性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无关联拼凑一起的大杂烩表现出来的,形式上的游戏反映了意义的去中心化,而这个中心指向白人主流文化。因此,他的作品反映了嬉戏与政治性并存的“双重符码”,从而撕下了后现代作品被贴上的“无深度”的标签。 三结语 摹仿,戏仿,伪戏仿三种美学策略显示了非裔美国文学由简单重复到创造性改造到语言文字游戏的渐次演变。摹仿是一种镜像隐喻,暴露了黑人文学对白人主流文学的依附,这种同质性的重复恰恰是后现代批判和颠覆的目标;在黑人文学传统内对原语言和原文本的戏仿创建了黑人文学的互文空间,在这个多元开放的体系内,意义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饱满的。同时,黑人作家们利用戏仿巧妙地将政治文化和种族等主题嵌入其作品之中,使之具有政治文化功能,戏仿因此成为解构单一文化模式的政治文化手段;而伪戏仿体现后现代的游戏原则,具有随意性、片段性和非中心性的特点。但对处于“第三空间”的黑人作家而言,“伪戏仿”并非纯粹的嬉戏和无目的狂欢,它仍保持着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在小说《芒博琼博》中,里德在戏仿西方侦探小说时,通过文类改写和价值重构将种族主体融入作品,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自身文化特色的侦探小说的变异模式。 当然,摹仿、戏仿、伪戏仿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曾提供了文化的动态模式,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着残留的、主导的和新兴的三种因素。威廉姆斯的文化模式为理解摹仿、戏仿、伪戏仿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三者常常共存,只是不同文学发展阶段各自占据的美学地位不同而已。事实上,在最初机械性的摹仿中,也有创造性的改造。比如,赫斯顿就认为布朗的《克洛特尔》决非拙劣摹仿,他对黑白混血儿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和追求自由的主体有别于同期的白人作家。而且,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一部小说中往往同时存在戏仿和伪戏仿,有时难以辨识出其中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比如上面提及的后现代小说家里德的作品中仍然存留着严肃性。如果说摹仿是童年的天性,那么戏仿则是具备一定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意欲彰显个性的成年人的手段,这两者与源物都有着一定的亲和性,而伪戏仿更像是变得“虚无”之后的成年人的兴之所至的文字漫游和某种意气用事的即兴组合,这时写作已然成为欲望释放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