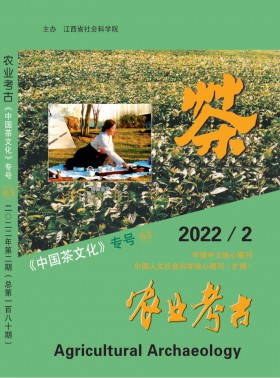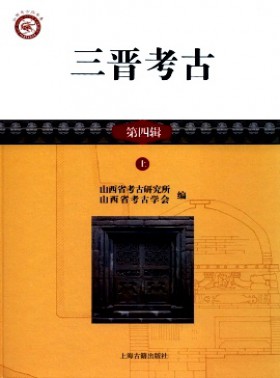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长耳双角,面目狰狞,钩尾处浮雕两条盘绕的小蛇。这件带钩线条流畅,做工精致细腻,怪兽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图7。参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兽形金带钩,钩钮甚大,钩体为一盘卧的怪兽,钩首似鱼头,双目镶嵌绿玉,钩身镶嵌有一硕大的螺状绿松石,钩身侧边镶嵌有曲尺形绿玉,口中吐出弯曲的钩首,造型独特精巧,为带钩中的精品。 汉代玉制带钩考古出土数量很多。 当时用玉之风盛行,玉雕技术精湛,是我国玉器制品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因此,玉带钩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龙虎并体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作龙首,龙虎连体,龙回首张口,衔一圆环,虎亦一爪夺环,钩体遍刻卷云纹,设计巧妙(图9)。同墓还出土一件龙首玉带钩,钩首为龙首,昂首挺胸,钩体圆雕龙爪,钩身有八节,中间六节用一根铁条贯穿,别具一格(图10。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一件白玉带钩,钩首为龙头,钩尾为虎头,钩体线刻卷云纹,钩背两端线刻四叶纹,纹饰简洁细腻(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p#分页标题#e# 江苏盱眙县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玉带钩,用白色半透明的玉制作而成,为长颈水禽造型,水禽双翅收拢,曲颈成钩首,腹部两侧分别刻有水波纹,雕刻十分细致(参朱安成《江苏盱眙县出土西汉玉带钩》,《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一件青玉带钩,钩首为鸭首且长过钩体,钩颈刻卷云纹,钩身刻有弧形纹,精巧别致(图11。参王恺之、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河北满城汉刘胜和其妻窦绾墓出土有五件小型带钩,用白玉雕琢而成,长度均不超过6厘米。刘胜墓出土的三件,玉质油润,白如羊脂。其中一件为秦汉时期典型的曲棒形(棒槌形)带钩(图12左);另一件钩尾似为牛角,上刻兽面纹,钩体弯曲,玉料有黑色杂质(图12中);还有一件为琵琶形,长5.8厘米,厚1.8厘米,钩首为龙首,龙角凸起,龙眼圆睁,钩体浮雕一蛇状兽,兽身周围刻卷云纹,该带钩整体造型别致,纹饰复杂,雕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玉雕工艺水平(图12右。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青玉带钩,长12厘米,钩体有灰褐色玉斑,钩首为龙首,纹饰简洁,仅在中脊刻有两条凸棱线条(图13)。安徽巢湖北头山一号西汉初年墓出土的两件龙形青白玉带钩,其中一件长14.6厘米,宽3.5厘米,厚0.9厘米,整体呈龙形,钩体扁平略作长方形,采用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制作工艺,钩首雕作龙首,钩体雕有六组变形蚕纹,左右两侧各透雕一只螭虎,虎头相对,左侧螭虎一后足与钩纽相连。 钩背光滑无纹饰。钩纽呈长方形,上刻有“中二”两字(图14)。同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青玉带钩,色偏黄,长17.8厘米,宽1.4厘米,厚0.9厘米,钩首作龙首,钩身为龙形。正面通体为浅浮雕蚕纹,钩体两侧线刻S型纹,钩背中间有一长方形纽,线刻变形云纹(图15、16。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处《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这两件带钩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均为汉代玉带钩中的精华。 秦汉时期的带钩造型种类丰富,题材广泛,有琵琶形、曲棒形(棒槌形)、鸭嘴形、兽面形、鱼形、贝壳形、圆钮形、龙形、牛头形、犀牛形等。无论什么造型,钩首一般都作动物首,如龙首、螭首、鸟首、鸭首等,其中大多制作精美。 在贵州威宁出土三件牛头形带钩,牛头形象逼真,同地又出土一件鲵形带钩,长10厘米,宽3.5厘米,整体造型为一游动的鲵形,头部及身体肥大,身有四足,四足正反面均有阴刻纹饰,线条朴拙随意,钩纽位于胸下,尾部渐细弯折向上为钩首,身体一侧阴刻隶书“日利八千万”五字。该带钩整体设计别致,刻画细腻(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一号墓出土一件鸭形铜带钩,钩首为鸭首,钩体为鸭身,鸭首扭颈回望,钩纽较大,呈喇叭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四川宝轮院汉代墓葬中出土两件错银犀牛形带钩,犀牛形态生动,制作精细(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圆钮型铜带钩,钩纽位于钩身末端,钩尾为圆钮形,上铸有两圈阳纹,阳纹中间夹有一圈棱型纹,钩首弧度较大,带钩整体设计简朴大方(图17。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9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尾分为双叉,酷似兔耳,十分奇特(图18。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中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带钩,钩首为兽首,张口呲目,钩尾塑一人,手持长棍形钩身,人物表情生动逗趣,动作活灵活现,似乎正在兴高采烈地奔跑中。整个带钩形象构思巧妙,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图19)。另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贝壳状带钩,钩尾作扇形贝壳状,并刻有棱纹和点状纹,较为少见(图20。参袁仲一主编《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秦兵马俑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所塑带钩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体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普遍使用,也促进了带钩制作工艺的进步。除了继承先秦时期铸造、镶嵌、浮雕、錾刻等技艺外,还大量使用错金银、鎏金银等工艺进行装饰。 错金银,主要是用于青铜器的装饰,即在铜器上铸或凿出所需纹样的凹槽,将金银丝或金银片嵌入凹槽内,然后锤实、错平,再进行抛光,使之浑为一体。错金银工艺,在我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流行,秦汉时期则更为成熟。河北满城县北庄东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银神人抱鱼带钩,钩体呈曲棒形(棒槌形),钩首为鸟首,钩尾作花朵状。鸟口衔一宝珠,怒目蹙眉,形象生动。钩身浮雕一鸟首人身的神人手抱鱼形象,神人长耳直竖,背有双翅,双臂抱鱼,口衔鱼吻,足踩蟾蜍,神人长冠顶端弯曲成为钩尾花朵的花瓣。带钩通体饰有错金银云纹、漩涡纹等,甚是华美。钩背有错银隶书文字“丙午钩口衔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神人手抱鱼形象,在汉代当有祈求长生、羽化升仙之意。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一件银地错金铜带钩,长11.9厘米,有铭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钩”(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省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江苏泰州新庄汉墓M3出土两件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为螭首,钩体遍布错金银纹饰,钩纽有仙鹤图纹,仙鹤振翅欲飞,栩栩如生,钩体有卷云纹,钩背有龙纹,且有嵌金铭文“五月丙午钩”,纹饰金银交错,精致华丽(参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年第10期)。带钩上“五月丙午”铭文,并非实际具体制造时间,或为当时一种祈求吉祥的套语(参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鎏金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即将金与水银的混合剂涂在铜器表面,随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了铜器的表面。我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到秦汉时期使用相当普及,不少带钩用鎏金技术进行装饰。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出土有两件鎏龙首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钩尾俱为龙首,钩身有四个镶嵌坑,惜所镶嵌之物已佚;另一件鎏金龙首铜带钩,钩身阴刻龙首纹饰(参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p#分页标题#e# 秦汉时期的带钩,往往饰有龙纹、云纹、四叶纹、缠枝纹、漩涡纹、蟠螭纹、龙首纹等。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铜带钩,钩首为龙首,钩身阴刻云龙纹(参《江苏省丹阳东汉墓》)。长沙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铜带钩,钩身遍刻缠枝纹(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带钩,其中一件为漩涡纹错金铜带钩,一件为龙首纹铜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2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首蛇首,钩体为琵琶形,饰有漩涡纹(图21。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带钩的创制、演变与服饰的变化直接相关。秦汉时期基本沿袭了战国的装束,带钩使用颇为盛行。秦汉时期带钩的造型设计、制作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汉以后带钩的使用逐渐减少,制作工艺水准也有所下降。秦汉时期的带钩体现了当时金属制作、玉石雕刻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等,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