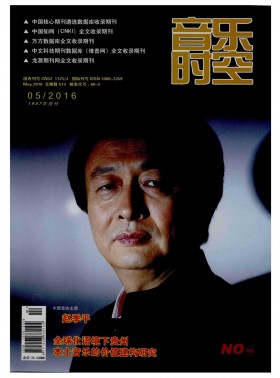作者:蔡之国 高凯 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悲剧影片虽然歌颂了两岸三地四个人的执著爱情,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极具悲剧性,是动荡时局、政治风云以及战争频仍等时代背景致使相爱之人不得不颠沛流离而隔海相望的命运悲剧。影片的开头是一艘在惊涛骇浪、凄风冷雨中摇曳的帆船,这是男主人公陈秋水在政局动荡时代背景下无奈逃离台湾的场景,与画面相谐和的则是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四季》之《冬》的急促而紧张的旋律——从音乐内部的运动来看,小提琴协奏曲《冬》F小调的第一乐章在和谐的背后具有极尖锐的不谐和,这种不谐和以留音、倚音、换音等方式出现,节奏急促,强弱鲜明——似乎暗喻着其与环境的艰难斗争,以及陈秋水颠沛流离的人生命运。秋水无奈的双眼望向远方,或许包含着他对动荡时局的无奈、对命运的无法把握、对爱情的艰难守望,而伴随这一场景的管弦乐,则在重复低音的演奏中力度逐渐加强,节奏日益加快,并最终在小提琴的独奏中得以爆发,而稍后乐队的低音重复和小提琴独奏交替出现,似乎预示着社会动荡的冷峻无情与个人感情的永恒持久间的矛盾即将展开,同时也象征着主人公命运的坎坷以及悲剧性的结尾。事实上,影片后面的影像叙事和乐音传播,似乎都是对开篇画面和乐音的具像性阐释,细致地揭示了男女主人公在大时代下的悲剧命运。
政治愿景的隐喻表达“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每个文本都是一种政治幻想,它以矛盾的方式连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内部构成个人的那种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关系。”④影视文本是潜隐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的话语叙述,甚或政治无意识往往充斥在文本叙述当中。《云水谣》屡屡被中央电视台宣扬的主要价值点可能就是其所包孕的家国统一的殷殷祈愿。陈秋水与王碧云一对有情人的“云水难交融”的根源在于大陆与台湾的不统一,这也是个人命运不幸坎坷的主因。影片最后通过一只雄鹰从陈秋水的墓碑上飞起,在西藏高原上自由翱翔后,然后越过千山万水径直飞往了台湾……与画面相配的则是管弦乐队演奏出的如颂歌般的高亢旋律,荡气回肠,气势恢宏磅礴,既是内心情感的迸发,更是深切情谊的呼唤。可以说,此处声画有机结合,用隐喻的方式传达出祖国大陆和中华民族深切呼唤游子重回祖国母亲怀抱,让分割在海峡两岸亲人重新聚首,让海峡分割的伤痕修复弥合的政治愿景。应该说,《云水谣》的音乐与画面有机结合,甚或独立于画面之外,传递出影片的主题意蕴,让人在唏嘘的感动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在视听盛宴中获得深层次的文化遐想。
用音乐塑造人物形象
“音乐在影视中主要是表达人物内心细腻的感情,当人物内心的情感难以用语言表达时,就是使用音乐最好的时候。”⑤音乐虽然是抽象无形的,但却既能表达情感的内容,又能表达情感的强度,是渲染情感、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云水谣》善于运用音乐对人物性格、内心情感等进行形象塑造,并实现了人物形象的情感性表现。
1.浓墨重彩的主角形象塑造先看女主公王碧云,当她在楼梯上与陈秋水初次相遇并擦身而过时,瞬间的顾盼生情在舒缓、柔情而又优雅华丽的音乐渲染下,引导观众在情感表达的张力中领悟到真爱的萌生与延续。伴随念唐诗、手影游戏等两人情意渐浓画面的是干净清脆的吉他声,而后小提琴声渐入,正当画面和声音正恣意酣畅之时,王母却发现了两人的私情,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营造出碧云感知危机到来的紧张不安。而老年的王碧云在得知朝思暮想的陈秋水永远葬身于雪山之下时,音乐极为低沉、忧伤,又间以尖锐轰鸣声,准确而贴切地表现出人物悲痛欲绝的心情,随后镜头慢慢推向欲哭无泪、极其悲伤的王碧云面部特写,而此时音乐顿时消失变为静默,这时具有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让观众在“空白”的音乐声中体会碧云的内心酸苦,正如波布克曾说的:“如果用的巧妙,悄无声息可以比金鼓齐鸣更有感染力。”⑥乐音与表达的情感内容相谐和,塑造出王碧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的内心情感和人物形象。再看男主人公陈秋水,在其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演奏或者歌唱的钢琴曲与英文歌,既体现了知识青年的修养,也表现出俏皮活泼的性格。“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当他被王母辞退回到家乡时,如画的乡间闲适的风景与一小段极富地方特色的小调吟唱结合,塑造出轻松欢快的乡间情调,但却反衬出陈秋水近乎失恋的愁苦心情。而在稍后的舒缓凄美并带有失落情调的音乐中,秋水失神地躺在碾米场的谷堆里,目光呆滞,神情忧伤,塑造出失恋中的陈秋水形象……而在西藏,当秋水听到护士讲有个“王碧云”来找他时,他不顾一切地扔掉扛在肩头的氧气罐,近乎失态般地一瘸一拐地四处奔跑、寻觅,与之结合的则是厚重、强烈、激昂高亢的音乐,表达出陈秋水内心的渴望情感;在两人即将相见之时,秋水满怀期待地深情凝视被单后的影子,乐声随之变得单纯细弱,缠绵深情,给人情牵一线之感;当陈秋水发现前来找到的“碧云”其实是王金娣时,音乐又厚重起来,表达出意外与震惊……这段2分27秒的音乐起承转合十分流畅,不着痕迹,并有效地塑造了主人公的内在心理与情感。
2.画龙点睛的配角形象塑造薛子路一直执著地爱着王碧云,无论是子路多次手持玫瑰在碧云家门口痴等、老年碧云再次见到子路的画像时所配的音乐,都是同一段单纯的吉他旋律,节奏简单,不加和弦,表现了子路对心爱之人的并不亚于主人公之间的纯洁之恋。玫瑰和吉他,这一反复出现的有形或无形意象,在视听两方面立体地塑造了子路的形象特征:执著而不善于表达。王碧云的父亲是一位风趣幽默的牙医,他为了心爱的女儿不顾森严的宵禁,驱车送女儿去见恋人最后一面。与吉他的抒情性相比,大提琴演奏的音乐更具叙述性:风声、雨声、雷声的自然场景与紧张低缓的大提琴声混杂,表现了一位睿智严父对女儿深沉的爱意;而当他说出“我真没想到你陈秋水是是左翼分子”时,大提琴的乐调又变为哀伤、连绵,乐音里隐含着作为父亲的意外与无奈。陈秋水的母亲出场的音乐持续时间虽短,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碧云追寻秋水来到西螺时,伴随陈母与碧云简短交谈的则是远处若有似无的具有母性基调的童谣声,将隐忍操劳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塑造;多年以后,陈母劝碧云别再等待,配乐忧伤略显凝滞,又饱含韧性,充分地展现了母性的柔情;临终前,陈母反复念叨秋水名字时,间以低沉、哀婉、凄凉的音乐,渲染出对儿子的绵绵思念,令人酸楚不已……最具象的画面和最抽象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很容易撼动观众的感官和心智,给人以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表达。电影音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曾指出:“银幕上的音乐能够挖掘出并强化角色的内在性格。它能将画面场景笼罩上特定的气氛:恐怖、壮丽、欢乐或悲惨。平淡的对话一经音乐的衬托便上升为诗意的境界。电影音乐不仅是联系银幕和观众的纽带,它包涵一切,将一切电影效果统一成一种奇特的体验。”⑦#p#分页标题#e#
用音乐转换时空
影视总是按照一定的美学原则对影视时空进行段落性叙述,而跨越时空的段落叙述不仅借助画面的衔接,还能借助声音实现自然过渡。影视音乐并不仅仅是表现情绪与思考,还具有“声音蒙太奇”的功能,用音乐转换时空,实现段落的有机衔接。电影《云水谣》的叙事时间长,穿越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时空跨度大,场景转换较多——纷乱人攘的台北古街、旖旎秀丽的西螺水乡、繁华的纽约与台湾、硝烟弥漫的战地医院、物资匮乏的西藏医院、小院、戏院、街头、公寓,雄浑壮美的雪域高原、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时尚暧昧的酒吧……而声音特别是音乐在里面承担着时空转换的作用,于是,音乐联缀了现实、回忆和想象的时间叙述,联缀了两岸三地的空间表达。比如《云水谣》的开场,在维瓦尔第《冬》音乐声中,场景由汹涌澎湃的江面转至繁华的曼哈顿上空、公寓,音乐也由急促尖锐变得华丽柔和,随之缓缓出现的是寓所里的小狗、美术作品,年迈的王碧云专心作画,音乐被电话铃声打断,她提起唱针,音乐戛然而止,影片进入现实的叙述阶段。停播唱片的动作使主观音乐成为场景音乐,也表明片头选用国际音乐的合理性,为继续使用西洋乐做铺垫。这一段从20世纪40年代的基隆到21世纪初的曼哈顿,时间空间跨度极大,但是音乐的运用却巧妙地实现了时空的跨越。再如在西螺,别后重逢的秋水和碧云畅谈、绘画、唱歌、洗发、看戏、拥抱、热吻,镜头不断叠化、转换,周围场景也不时变化,影片创作者消去同期声而改用配乐,碧云清唱起英文歌,两人合唱,音乐闪回,是老年碧云回忆时的甜蜜与遥远的表情。这些都在舒缓柔美音乐声中悄然转换,浑然天成,不觉突兀。而影片中从朝鲜战场切换到祖国大陆时,时代背景已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音乐一改先前的低沉、急促,以昂扬的旋律促人奋进。民族的崛起,抗争压迫的胜利、国家命运的改变使个人的奋斗有了目标。青年人愿意舍弃自己的青春、生命,奉献给伟大的祖国。这些情感在作为背景音乐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片尾的镜头则用音乐将空间进行了有机衔接:腾空而出一只飞鹰从陈秋水、王金娣的墓碑升起,宏大、悲怆的主题音乐响起,苍鹰迅速移动在浩荡长天上,俯瞰大地,跨越山河,冲向云霄,最终定格在地图之上的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这一连串的画面转换之中,人们很容易被极具表现力和情感张力的音乐所牵引所震撼,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影片传递的价值观。利用音乐转换场景,连缀时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利用视觉和听觉的不一致,而冲破画框的局限,将画框内外甚或画面和画面连为一体,从而使时空获得自然转换;二是为画面配以典型的时代性、地方性甚或于人物有典型或者特殊意义的音乐,能够引发人们的联想,将人们的思维由画内带到画外,将画面和声音所表现的时空联系在一起,产生更大的时空和更深广的文化意义。
用音乐表现多元化风格
剧作情节的推进、人物情感的变化以及时空的跨越,都使得音乐很难一曲而终,而是根据地域、场景、情感以及剧作的需要采用多元化的音乐。《云水谣》由于时空跨越大,故事情节变换较快,人物情感波折起伏,这使得片中的音乐的样式、节奏、主题不仅丰富多彩,而且还与时代和地域、国际与民族等音乐特征融合成一体,体现出多元化的艺术风格。
1.音乐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影片的音乐不仅符合主题的表现、人物形象的塑造,还具有国际化和民族性特征,表现出球土化传播的努力。影片选用了一些外国音乐来表现人物形象,塑造影视氛围,既有古典音乐如维瓦尔第的《冬》,也有经典影片的电影音乐,如美国音乐传记片《翠堤春晓》主题曲《whenwewereyoung》。前者符合王碧云大家闺秀和留洋艺术家的身份,而后者本来描写的就是卡拉和斯特劳斯之间的爱情,因此,陈秋水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时,既是对王碧云爱慕的含蓄表达,也符合英语教师的身份,成为两人爱情的融合点和主旋律,以及日后热恋、相思、结束的见证。不仅如此,《云水谣》还选集和运用了一些民族化的音乐,如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联欢,唱着快板和鼓舞士气的歌,其中有一段《苏三起解》的京剧表演作为背景音乐。京剧是中国国粹,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体现了军民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也贴近志愿军指战员的本土生活。应该说,音乐除了强调环境的真实、起到标识环境的客观作用外,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甚或以一种假定的真实表现出艺术表达的作用。
2.音乐的地方性与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音乐,也表现出不同的音乐意义。影片开场有着一段被奥斯卡大导演奥利弗•斯通极力赞扬的6分钟长镜头,巧妙地将闽南戏、婚嫁、大街小贩、国民党士兵等台湾20世纪40年代的民俗景象呈现出来:擦皮鞋的声音、远处汽车开动的声音、叫卖的声音、唱戏的声音、鸽子飞的声音等,站在阳台上的女人唱芗戏,随着镜头慢慢升起,唱戏的声音渐隐,布袋戏再渐显,布袋戏很到位地营造了那个时代的氛围。陈秋水、薛子路的几次见面,大街上若有似无地放着当时流行的唱片,也极具生活气息。而陈秋水和王金娣结婚的时候,热情的西藏群众伴随着欢快的《洗衣歌》载歌载舞,来庆祝他们的婚礼。《洗衣歌》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不但能衬托出婚礼场面的喜庆,更符合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陈秋水、王金娣的雪山遇难,则采用佛乐《六字大悲咒》,秋水背着金娣在雪地中艰难地行走的画面,间以两人婚后幸福生活镜头的闪回呈现,而藏族女歌手日雍思曼以悲怆感伤的哭腔来清唱,歌曲悠扬而渺远,空灵而伤感,既具有地域性也具有表情表意性。应该说,《云水谣》糅杂着宝岛台湾的闽南戏、布袋戏、民间小曲、流行曲《望春风》和《雨夜花》,也有京剧名段《苏三起解》,还有藏族的佛乐《六字大悲咒》、歌曲《洗衣歌》、《北京的金山上》等,以及抗美援朝歌曲《慰问志愿军小唱》(几次战役打得好,咱们出现好汉和英雄,好汉英雄真勇敢那,英雄好汉立了功……)、《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呀……)、数来宝《战士之家》(大豆腐、小豆腐、干豆腐、水豆腐、油炸豆腐冻豆腐……)、雄壮嘹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这些都极好地建构出影视叙事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具有再现性和表现性艺术效果。#p#分页标题#e#
3.音乐形式的多样性《云水谣》的音乐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现场的同期声,也有后期艺术加工的音乐;既有独唱、清唱、合唱,也有男声、女声、童声;既有节奏的激昂高亢,也有乐音的哀伤低沉;既有民族乐器的乐声,也有西洋乐器,甚或有中西合奏的乐音。而音乐或作背景或作主题,或表现人物或引发联想……每首音乐都颇具匠心,创作者并不只是把素材拿过来,还精心将素材改造成那个时代的文化意蕴,例如在山洞里演出的那场戏中有一首《慰问志愿军小唱》,是创作者郑春雨精心选用了1952年出版的歌本,带领乐队反复排练才最终录制而成。《云水谣》中的音乐与剧情与画面很好地融入成一体,营造了真实的历史、社会和生活氛围,水乳交融地推动着故事剧情的发展,刻画着人物形象,映照着影视创作人员的主题思想,实现着影视艺术视听结合的艺术魅力。
结语
美国著名导演弗•科波拉说:“音乐是电影幻觉的生命。”法国著名导演帕•谢罗说:“一部影片若无音乐,就如同一只脚走路。所以若要我回到没有音乐的年代,我宁肯不拍电影。”⑧《云水谣》影片不仅仅描述了真挚执著的爱情,更有对两岸间政治愿景的表达。该影片音乐元素与所展现的精神内核相辅相成,使观众的精神得到洗礼,爱国主义得以弘扬。从影片中舒缓或悲壮或感人的音乐里,唤起人们精神的奋发、内心的震撼,把观众推向电影所营造的最高境界,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