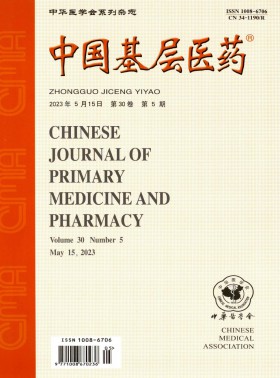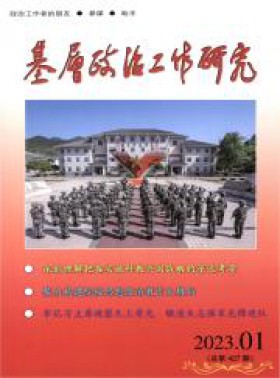贾樟柯自称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1],他将这一立场始终贯穿在几乎他所有的作品之中,他“用满怀深情的目光凝视着被时代浪潮所改变的人生与生活,并发掘出底层群体在变迁中所呈现的饱满的生命力量”[2]。贾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音表达,流露着极具纪实风格的美学气息,其中对声音的创造性使用渗透了他的想象和激情,表达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笔者悉心于电影的声音,着力尝试深化贾樟柯的电影不只可以看,更可以听的独特意义,从他电影中嘈杂的同期环境音、流行音乐、大量的方言,甚至“无声”的静默,探听到中国社会底层的日常生存现实,并感受其中散发的底层文化特征。 一、探听真实的底层环境声音 环境音通常以同期声的形式展现于电影中,它的作用在于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声音状态,使视觉形象获得强烈的现场感。充斥于贾樟柯影片中的各种环境音:广播声、汽笛声、马达声、高音喇叭、电视声,都再现着真实的底层环境,观众可以最大音量地探听到原生态的底层声音。 《小武》中几乎保留了所有的同期声:自行车铃声、汽车引擎声、嘈杂的人声以及广播声等,这些声音都构成了来自底层最基本的乡土气息。 这些都向我们传达着县城——这个中国社会典型的底层群体单位的百姓的生活,暗示着底层社会人物与大环境的冲突,发人深思。当小武回农村老家时,乡村广播里正把香港回归的讯息与乡民卖猪肉的广告并列播出,形成一种奇妙的声音蒙太奇——转接出一种上层建筑与底层生活的无奈和谐。在影片结尾,小武被抓捕后铐在路边,自行车铃声、汽车引擎声、嘈杂的人声又重新响起,而此刻听到的惆怅和愤怒,已不再是小偷特有的,观众会发现底层的小武不是汾阳特产,他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他5分钟的短片《狗的状况》中我们听到麻袋里小狗依依呀呀的呻吟,似乎正是底层生活深刻的声音——为生而挣扎。《世界》中有很多这样的零星声音,赵涛胳膊上一直带着一个铃铛,叮铃叮铃的一直在响,这与狗身上挂的铃铛并无差别,声声作响中听到的是一种来自底层的害怕,害怕自己迷失,时刻用这样的声音证明自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贾樟柯电影中多处出现过诸如火车鸣笛声、飞机起飞声、卡车轰鸣声、轮船鸣笛声、甚至拖拉机的马达运转声等交通工具启动、行进的声音,这些声音的反复出现显得意味深长,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社会奔波的声音,声音源自他们内心的向往,向往着离开、逃脱和改变。在《站台》里,崔明亮一伙人追赶火车的一幕着实感人,火车远去拉长的笛音在观众耳畔里久久不能消去,这是梦想朴实无华的张扬,随着火车笛音和他们大声的嘶喊飘散在空气里但当影片结束时水烧开的茶壶发出像极了火车鸣笛的声响时,我们被这个声音刺痛了内心,我们探听到底层的这种声音——来不及感觉冲突,只有无奈。《三峡好人》中经常可以听到重锤拆迁的沉闷响声,观众可以从中探听到沉睡的集体鼾声,也可以听到一两个生命在梦中觉醒,但又回头睡去。这恰好和世界中的铃铛声配合的相得益彰,丰富了整个贾樟柯电影的声音组合,而这些声音其实正好构成了两个字,那就是“世界”。 可以说,贾樟柯电影中那些几乎出现在每个场面里的粗糙的混响音效在配合故事推进的同时都直观反映出全方位转型中的当下中国底层的社会文化以及我们生存的空间的喧嚣、躁动。贾樟柯坚持大量运用各种尘世噪音来代替语言渲染环境,表现人物心理,表现当代底层生活中难有平静和安宁的时候。这种让我们觉得乱七八糟的从头到尾没有停止过的巨大噪音,在贾樟柯的电影里直接呈现了变化的主题变化在这些声音中发生,一些东西消失了,或被破坏了,但声音却在持续。[3]也正因为这种持续性,才提供了我们探听底层声音的可能性和深远意义。 二、探听以音乐为代表的大众 媒介文化在底层世界的真实唱响依靠大众传媒,流行文化被运作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中国本土地自动地被再生产。这些流行文化反映了充满活力又很粗糙的底层生存状态,表明媒介虽构造了一个世界共享的视听空间,可现实生活空间却存在天壤之别。音乐这种最具代表性的大众媒介文化,不仅仅是供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时候音乐是在大街小巷的嘈杂声音中灌输给我们的,这才是音乐真实的呈现面貌。从这一点出发,观众可以探听到大众媒介文化在底层世界的真实唱响。 这一点在《站台》中体现的非常突出:《站台》的时间横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描绘了底层边缘的真实变迁,其中很多音乐都是社会转型期底层社会的真实唱响。开场的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是典型的革命文艺,滑稽的表演方式充满了集体主义的乐观。“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的地方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4]电影中用了很多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如《站台》、《在希望的田野上》、《美酒加咖啡》、《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春啊,青春》、《是否》、《好人一生平安》等。“我们从这些老歌里获得了某种认同,好像就是认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娱乐方式老歌记录历史,老歌表现现实老歌的功能已经有了从宣传到娱乐的转变,这正如文工团的体制改变了一样。”[5]。可以说,《站台》是考察结束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标本,是底层生活的反娱乐化唱响,再现了包括变迁、迷茫、向往、灼痛等在内的真实的底层文化特征。 《任逍遥》中歌曲《任逍遥》贯穿影片始终:“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强调个体的欲望感受和个性张扬的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价值观,赢得了影片中几名底层小人物下意识的拥护。 不断插入的主流媒体的严肃的电视新闻播报不仅交代时间线索,更传达出权利话语的舆论指向。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源构成了一个含混的意义混合体,对无业少年的精神世界共同产生着影响。但只是听,会发现这些信息源并不负责解决底层生活的困境和提供一个实在的出路,因而个性的觉醒与底层生活的沉闷之间最终产生了冲突。这指出了流行文化包裹下的社会不能摆脱贫困和压抑的阴影。[6]如果说在《站台》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变迁,那在《任逍遥》中无疑听到的是直截了当的冲突、反差,音乐唱响后回荡出的是对底层现状无尽的反思,以及对真实的反思。#p#分页标题#e# 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文化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在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听到各种来自底层的大众媒介声音,不论是政治话语或者流行文化,都像是一种被重新唤起的诉说,用真实的语调娓娓道来,让听者又平静又慌张。如贾樟柯自己所说:“我就是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普通民众的趣味中,我感受到了人们朴素的希望以及朴素本身所具有的悲剧力量。”[7]他还在访谈中这样说:“我只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转型时期,变化是非常大的,对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真实的民间影响,我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留下这个年代、这一刻的真实的影像和声音,作为一种文献,至少作为一种文献保留下来。”[8]我们从这些流行音乐中可以探听到底层人在追求自由状态的过程中情感都是受到压抑的,他用影音刻画了底层纪实,也记录了当时时代典型的底层文化特征。 三、探听方言充斥的底层对话 方言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语言,是一种地域文化外在的标记,沉淀着某一地域群体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折射着底层群体成员现时的社会心态、文化观点、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方言在电影中运用,贾樟柯不是先例,但在影片中全部使用方言,贾樟柯算是第一人,在他的电影中有河南、山西、北京、四川、东北、上海方言等。“用方言进行表演能增加影片里的现实氛围,因为在那个小县城的日常生活里,人们很少会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跟别人进行交流。”[9]其实,一个人在说方言的时候往往才能更流利痛快地、准确地表达自己。影片运用方言式的对白,让我们直接地探听到完全原生态的底层对话,以及对话内容中真实的底层声音。 首先,方言充斥的对话,道出的是底层社会在经济冲击下的变迁,是底层的对话,以及变迁中根与自由的自我辩论。具体来听,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全部使用山西方言,而《世界》也以山西方言为主,间以温州话、俄语和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其中导演将北京世界公园这个有着多重隐喻意味的人造景观作为叙事场所,讲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大批涌入城市却不是城市主人的外来打工者的故事,将普通人的生存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直接深入底层社会的肌理,深刻揭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正处在一个意识杂陈、文化拼贴的境地。其中主角的山西方言与公园高音喇叭发出的无地域特征的强势的普通话形成鲜明对比:方言这种边缘性的语言和信息载体在这里成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不合拍的象征,传递着贫困与落后。而太生对在工地上打工的同乡三赖很快就能用普通话交流感到十分惊讶,边缘文化竭力向主流文化靠近的努力显而易见。而以三峡工程、三线建设等宏大叙事为背景展示个体命运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中也是四川方言、山西方言和普通话相混杂。 在贾樟柯的声音策略中,方言的运用形成了一个本地化亚文化圈,与此对照,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广播影视等传出的标准普通话则成为一种远离人物现实生活的主流社会的象征。他刻意将方言和普通话并陈来制造一种疏离的效果,凸现底层小人物与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隔膜。 四、探听无声的静默 有时候“无声”也是一种声音美学,安静地倾听静默,听到的是空气中无声的力量。贾樟柯的电影中经常会有长时间的静默,像是一种致敬,像是一种沉思,亦像是一种宏大叙事收拢后的内心潮涌,我们从中探听到来自底层的沉默,和沉默中的叹息、面对、茫然、怅惘以及更多的习以为常。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静默的长镜头,人物或者景物在无声中安静的存在,观众可以用眼睛看,也可以用心听,在静默中往往会听到更多的声音。空气和静物都带着安静的丰富内涵,探听无声的静默,是一种对底层真诚的思考。 《三峡好人》中贾樟柯通过现实生活噪音唤起的是远景中江水、云彩等自然景观的静默,而远方的沉默又融入中国现实巨变中的混杂和喧嚣。《三峡好人》的英文译名“StillLife”,可以和贾樟柯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文学式阐释对应起来:(我)有一天闯入一间无人的房间,看到主人桌子上布满尘土的物品,似乎突然发现了静物的秘密,那些长年不变的摆设,桌子上布满灰尘的器物,窗台上的酒瓶,墙上的饰物都突然具有了一种忧伤的诗意。无声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10]底层社会中,嘈杂与安静总是相对的,安静背后往往酝酿着不安的躁动,而嘈杂背后也总是留有一片安宁,这需要我们细心探听。在某种意义上,对静默的特别迷恋是与贾樟柯的纪实冲动有关,他对那些其生存如静物一样寂静的人肃然起敬。从静默中探听到的底层空旷的声音,为贾樟柯电影摄制提供了种种可能性,他的电影既是消逝的诗学,同时也是拯救的纪实。 静默会被粗心的忽略,也会成为一个焦点,所有意象、声音、故事都朝它聚拢汇集。 无声是一种冷静,通过近乎残忍的无声,记录着一个巨大社会转型时代一般老百姓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发生的转变,探听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面貌——在物欲横飞的历史进程中被无情地冲撞、迷失,然后没有知觉。我们正是通过探听底层的声音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在急速发展的状态下存在的问题。无声让我们感觉到一些美好的事物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底层群体的生存正在变得岌岌可危,一些无形的东西:理想主义、梦想、安全感、归属感、方向感、准则在正在消失,这是一种忍受着的无声的暴力。每一场电影结束都会回到一片安静,在安静中我们可以听到:电影完结了,人生还在继续。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电影由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新艺术,贾樟柯的影片正是通过各种杂乱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共同阐述了现代人被各种声音和影像所侵扰的生活实质。用心探听,我们可以发现贾樟柯电影非常可贵地运用了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被忽略和被遮蔽的生活,他将关注的目光伸向了“沉默的大多数”,透过其影像中的芸芸众生,我们可以听到真实的中国人,真实的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贾樟柯的电影中的人物都居于社会的底层,影片真诚记录了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让他们走出被遮蔽的角落,走进了观众的视线,观众也由此听到了长久以来被主流话语淹没的个体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苦闷和迷惘。贾樟柯的电影不只可以看,更可以听,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通过声音巧妙运用,帮助我们从中探听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一种真实的生命。#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