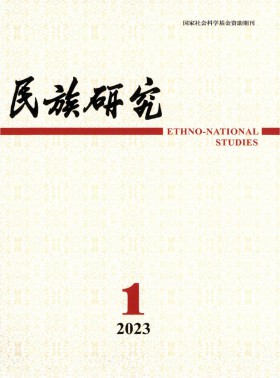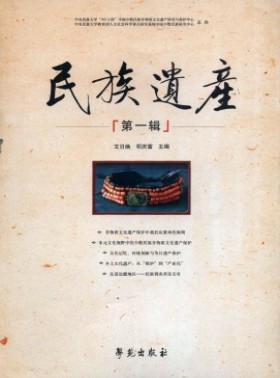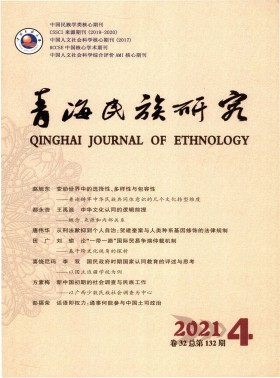在民族大迁徙运动的强烈影响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文化争奇斗艳、众多民族角逐争衡的时期。这个时期流行的宗教文化有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祆教文化、道教文化、摩尼教文化和景教文化等,其中佛教文化为主导。当时新疆佛教文化变迁与民族演变极富特色,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一、该时期新疆佛教文化的特征 自佛教传入后,新疆各地许多王公贵族即皈依佛门,并为宣传佛教而摇旗呐喊,普通民众也纷纷选择佛教作为其精神寄托。这样,佛教在新疆各地的传播势如破竹,迅速取代了原先的原始宗教的主导地位,成为人们新的信仰中心、精神支柱和文化选择。“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家家门前皆起小塔,……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②“宗信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③这样的佛教盛况在当时的新疆各绿洲城国十分普遍。 作为新疆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在古代新疆的传播有个地方化、民族化的过程。由于各地佛教传入时间和路径有异,所用经典有别,并且传入的佛教文化与当地原始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及其他宗教文化(祆教文化、摩尼教文化等)要发生冲突、调适、融合,因而当时新疆佛教文化有鲜明的各地方化和各民族性的特点,其文化结构是多元的。例如,当时为了更便捷地传播佛教,龟兹佛学大师佛图澄以观天象定吉凶、命龙王出水降雨、与天神交往等方式,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以广吸徒众。①佛图澄就把当地原始巫术融入了佛教,从而开创了中国佛教密宗的先声。② 这个时期新疆各地普遍流行“般遮于瑟”大会(又称五年大会、无遮大会)。“般遮于瑟”大会上以各种艺术形式宣传和演绎佛教的理义,尤其用戏剧、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形式表现佛陀的种种圣迹,受到信众的热烈欢迎。这种形式在于阗、龟兹非常盛行。③公元4世纪末,中原僧人法显在于阗亲睹了大会上“行像”的重大场面。④而唐玄奘在游历龟兹时也看到了其壮观的场景:“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物,奉持斋戒,受经听发,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以锦琦……动以千数,云集会所。”⑤ 当时新疆各地都有规模宏大的译经活动。古代佛典主要译自汉文、各种印度和中亚语文(主要是梵文、粟特文)、古高昌文、突厥文等。涌现出了许多非常杰出的佛教翻译大师,如白延、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实叉难陀等。除佛经外,还有众多的佛教颂词、小说、剧本等。佛教文学的繁荣,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还对某些民族文字的创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艺术是佛教观念与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佛教情感的艺术表现,是赋有艺术美外形的佛教精神。新疆佛教艺术是多文化成果的结晶,具有十分突出的混融性特征。佛教雕塑艺术是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本地文化的融合体;佛教绘画艺术闪烁着印度、希腊、中原、西亚及本地艺术灵感的火花;佛教石窟寺院建筑艺术也深受印度、中亚及中原风格的影响;佛教舞乐文化更是在充分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一体,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疆佛教文化在广泛吸取印度、中亚、中原等地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其旺盛的创新精神,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新疆佛教文化,并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楼兰(鄯善)、高昌五个佛教文化中心。但是各地和各时期的佛教文化并不一致,体现了当时新疆佛教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二、该时期新疆民族演变的特征 这个时期是新疆民族大迁徙运动的时期,活跃在新疆的古代民族除了原住民族外,还出现了释迦、鲜卑、柔然、高车、嵕哒、悦般、吐谷浑、铁勒、突厥、突骑施、葛逻禄、样蘑、黠戛斯、吐蕃、回鹘等部族或民族。不同部族或民族的居民进入新疆,使新疆的人种和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化了。随之在新疆一直发生着复杂的民族演变,一些原住民族及迁入民族由于融合其他民族或与其他民族组合而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体在形成之中,民族的分化也在进行之中。 这个时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羌人的主导地位被塞人所取代了,羌人、塞人、月氏人内部及其之间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民族组合、同化和分化。天山以北及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各民族之间经历了一个铁勒化的过程。隋唐时期,突骑施人、葛逻禄人、样蘑人进入塔里木绿洲定居区,并开始强烈地影响着新疆的民族格局。回鹘西迁后,铁勒化转向了回鹘化,新疆全方位的民族演变在积极而剧烈的酝酿之中。 这个时期新疆民族演变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塔里木盆地羌人和塞人地位此消彼长。秦汉以前,羌人一度在塔里木盆地占主导地位,建立了很多“城郭之国”。然而随着更多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中亚塞人东迁,以及北印度一些部族(如贵霜等)进入于阗,羌人逐渐在政治上以及人口上处于劣势。过定居生活或与塞人杂居的羌人、月氏人渐渐同化于塞人之中;而过游牧生活的羌人仍保持着其民族特性,不过其活动地域和活动能量已经日益缩减了。 其二,9世纪中期之前其他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民族,并未能对此地的人种和民族形成大的冲击。5世纪中期,羌化的鲜卑遗族吐谷浑人进入新疆,鄯善和且末成为他们的领地,但他们主要和羌人杂居在一起,羌化特征更为明显。7世纪中期后,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吐蕃人进入新疆,一直到公元866年。吐蕃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进入南疆地区的吐蕃部落,对于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南下绿洲其他游牧民族虽然以武力取得了一时的优势,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以较高文明所征服”,①这些游牧民族几乎均被当地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所同化。#p#分页标题#e# 其三,魏晋南北朝时,印欧语民族(主要是塞人)已经在塔里木盆地多数绿洲上取得了优势,隋唐时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展到几乎整个南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羌人、月氏人、粟特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参加了复杂的民族演变过程。一些较大的,包含了更为庞杂人种和民族的中心城邦国家开始出现了,以前的36国合并为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鄯善、高昌六国,并且人种、文化在进一步的整合过程中已逐渐趋于一致。 其四,魏晋时期,新疆各地的汉人渐渐集拢于高昌,后又有更多的汉人从中原迁来,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以汉人为主体的生活区域。②公元327年前凉的张骏在此设昌郡,推行中原郡县制。公元442年北凉王族后裔沮渠无讳率一万余户人在高昌称王。虽然沮渠氏本匈奴种,但实际上是早已受汉文化熏陶而同化了的准汉人了,其部族也已汉化。公元450年沮渠安周消灭了车师前部政权,残部西迁焉耆,留居者则以车姓融入汉人之中。从公元460年起高昌进入高昌王国时代,历阚氏、张氏、马氏、麹氏四个家族统治。回鹘西迁高昌后,此地的汉人及其他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重组,逐渐融入了回鹘之中。 其五,魏晋时期,中亚粟特人开始在新疆形成规模相对较大的居留地,并且积极地加入了新疆民族演变的行列。此时某些粟特人已成为塔里木盆地一些地区的统治者,如末国的国王姓安,是粟特九姓的安国人,因古柯(今莎车)的统治者也是粟特人的相貌。①粟特人为新疆其他民族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对新疆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来这些粟特人逐渐融合于新疆当地民族之中了。 其六,主要在天山以北活动的鲜卑、柔然、高车、悦般、铁勒、突厥、突骑施、葛逻禄、样蘑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和存在时间极不稳定,骤兴骤灭,大部分参与了当时新疆复杂的民族演变过程,这些民族以后均不见于史,基本上都是以不同形式融于新组成的民族集合体中。一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铁勒化的浪潮。 其七,隋唐时期,进入塔里木盆地属于突厥语族的突骑施人、葛逻禄人、样蘑人已开始从语言、文化、血源等方面强烈影响当地民族,使当地的民族分布及文化发展格局发生改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突厥化趋势。② 其八,回鹘西迁后,由于在人数、政治、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铁勒化、突厥化转向了回鹘化,大的民族变动正是积极的运作之中。这为以后维吾尔族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语言、地域、文化和心理的准备。 三、该时期新疆佛教文化对民族演变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对民族演变影响的主要特征是,佛教文化促进了新疆绿洲定居区的民族融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方便和加深了被沙漠分割包围的各个绿洲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交往和交流,各绿洲人民处于极为密切的互动和相互渗透之中。由于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各绿洲人民不时处于迁徙流动之中,而相同的信仰和类似的文化有利于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和确认。 其二,佛教是一种与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更相适应的宗教文化,普遍“造招提僧纺”③是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之一。而佛教寺院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在佛教徒中享有神圣的地位,佛教徒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佛事活动,如当时新疆各地的佛教行像活动便是如此。这些包括佛教寺院在内的佛教圣地对其影响之下的教民无疑起到了共同地域的确认作用。法显记叙了当时于阗一座宏伟的佛教寺院,“……作来八十年,历三王方成……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着少。”④可见这座寺院为当时岭东诸国所共同尊奉。 其三,佛教文化对新疆各地的语言文字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以各种字体书写的梵语、汉语、犍陀罗语、帕提亚语、普拉克利特语等佛典流行于新疆各地,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人们与文字打交道的机会。还没文字的当地人就用梵文等原文来抄写佛典。当地人对文字熟悉以后,慢慢试着用佛典所用的文字来解读自己的语言,这样就开创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事实上第一次把大众部连同佉卢文和犍陀罗语一起带到了和田,而第二次将说一切有部连同佛教混合梵语和婆逻谜文一起带到了那里。”①从2世纪开始,于阗已经流行表达犍陀罗语的佉卢文,但由于与于阗俗语差距很大而未深入民间,至公元5世纪时衰落。3世纪时佉卢文和犍陀罗语东传到鄯善,佉卢文成为鄯善国的官方文字,当地人操渗透了大量当地吐火罗语方言———楼兰语词汇的犍陀罗语。后来婆逻谜文流行了起来,包括图木舒克语、于阗语、扜弥语在内的塞语用直体婆逻谜文字书写,包括龟兹语(吐火罗语A)和焉耆———高昌语(吐火罗语B)在内的吐火罗语则用斜体婆逻谜文字书写,在邻近地区吐火罗语的长期浸润下,鄯善人慢慢忘却了犍陀罗语而改操吐火罗语了。由于使用了相同的文字,在长期的相互借鉴、吸收、融合过程中,不仅塞语、吐火罗语各方言之间,而且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了,共同的语言在更大地域和更多民族中逐步确立。 其四,受佛教文化及信仰的长期影响,各绿洲人们之间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进一步趋同。共同的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有利于各个较大地域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利于文化和心理素质的重组和整合。 由此可见,佛教文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为这个时期新疆绿洲定居区的民族组合、同化及分化创造了客观条件。秦汉时数十个“城郭之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合并到六个,这正是民族融合重组的客观反映。发展较迟缓的定居羌人、小月氏人等逐步同化于塞人、吐火罗人之中,或者与这些民族发生民族组合,后来一部分吐蕃人也加入了这个过程之中。包括一部分高昌地区的车师人、匈奴人等则融入了汉族之中,形成了一个操汉语、盛行汉传佛教文化的高昌汉人群体。建立在佛教文化基础上的高昌回鹘文化,大大加快了回鹘文明进程,当他们的文明程度高于当地或邻近地区其他民族时,他们的文化就对其他民族有吸引力,促使其他民族学习、应用回鹘文化。随着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形态慢慢与回鹘人趋于一致,这些民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回鹘化的道路。同时,民族分化也在进行之中,如流行佛教文化过定居生活的羌人融入了塞人、吐火罗人,而流行原始宗教文化过游牧生活的羌人则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改奉佛教的塞人加入了新疆绿洲定居区民族组合浪潮中,而流行祆教文化过游牧生活的塞人则继续以原先的民族集合体留居在中亚等地。不同文化的影响导致了这些民族不同群体的异向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该时期新疆民族演变对佛教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新疆民族演变对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新疆绿洲定居区,几大佛教中心的佛教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于阗、高昌主要流行大乘佛教文化,疏勒、龟兹、焉耆主要流行小乘佛教文化。各地的佛教音乐、舞蹈也不尽相同,如龟兹乐主要是在印度佛教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中原雅乐和本地羌人古乐融合而成的一种具有浓厚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音乐体系;而疏勒乐的源头则是波斯的祆教音乐与本地的佛教音乐结合的产物。其他诸乐也各有其渊源。各地壁画、石窟的风格也呈现出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各地文字虽然都是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创立的,但依据本地条件,各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些佛教文化方面差异的形成,主要是不同民族将其各自的固有文化与佛教文化结合的产物。 其二,汉人在新疆的活动,不仅直接参与了民族演变过程,还对当地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都通行汉文,这对加强各地的往来交流,对传播和发展佛教文化,起了促进作用。各地佛教文化深受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高昌、于阗和后期的龟兹等地。如在龟兹的库木吐拉石窟中,从壁画风格上可以看出浓郁的汉风。第12窟、15窟壁画上所绘的菩萨像,头戴小型化鬓冠,高发鬓,胸前饰有复杂的细璎珞,人物显出“其势圈转,画衣服飘举”,这样的风格已是盛唐以后中原各地石窟中菩萨造像的标准形态。①这个时期的高昌佛教文化既有浓厚的汉传佛教文化的特点,又呈现出车师佛教文化、龟兹佛教文化的风格。这种以汉文化为主导,兼容多种文化的佛教文化在当时西域独具特色,并强烈地影响了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佛教文化。 其三,回鹘佛教文化的混融性特征极为明显。回鹘西迁以后,回鹘王国境内的汉人、印欧语诸民族、铁勒诸部逐渐融入到了回鹘之中。回鹘佛教文化充分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成分,同时回鹘佛教文化又博纳了摩尼教文化、景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祆教文化等多种宗教文化因素。高昌人广泛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文化要素,把他们结合起来为己所用。发现于吐鲁番的一种历书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该历书用粟特语写成,每日同时记有相应的粟特语七曜日名称和中国的天干及与之相配的突厥式十二兽名,然后再用粟特语把中国的五行名称也译写在上面。一份历书之中就结合了粟特、突厥和汉民族的不同文化,可见回鹘文明的开放性和极强的接受能力。有人形容说,吐鲁番好像是一块海绵,它从各个方面吸收精神内容与文字形式。②同样,回鹘佛教文化的混融性特征更为凸显,使得其佛教文化更富有生机与活力。如“畏吾儿人崇拜偶像(but-parasti,佛教),原因在于那时候他们会巫术,行使巫术的人,他们称之为珊蛮(qam)”,③这便是佛教融合萨满教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