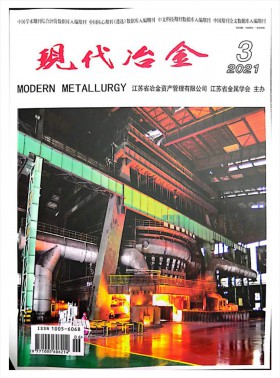对当前文化理解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的反省
在文化理解上概念林立、莫衷一是是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经典性难题,出现这一情况不仅和文化概念自身指涉对象的模糊、外延的泛化波动有关,而且还和研究者所引入的视角日趋多样化有关。这一研究局面的形成也表明:文化学研究正值风华正茂、青春年少之时,对文化事象的研究具有无穷潜力,它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加入。年轻既是一事物生命力正值强壮的时代,又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对文化事象的探究就处在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上。实际上,各种文化理解都是表层的文化概念表述与潜层的认识倾向的统一,在文化理解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倾向潜在地引领着文化研究的路向。在这些倾向中,既有正向、积极的倾向,也有负向、消极的倾向,对这些倾向及时进行分析和澄清是确保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结合图1,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文化理解的不良倾向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实体化倾向
文化的实体包括有形实体和无形实体两种,前者涉及文化的事物、现象、(物理性)符号等,后者涉及文化的意象、象征、概念等,文化就是这两种实体在有机联结、动态平衡中构成的有机体。在文化理解中,如果对上述两种实体的关系处置不当,就极有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实体化的认识倾向,最终使文化存在物内在的平衡与关联发生失衡与失序。譬如,如若对文化的有形实体部分强调过度,就会导致一种见表不见里的肤浅文化概念产生。反之,如若对后一种实体过度偏重,就可能将文化这一具体存在物“还原”为理性的概念“结晶体”,真实而又自然的文化形态随之被过滤掉了。总而言之,前一种文化概念的产生源自其只用肉眼来“看”,后一种文化概念的产生源自其只用理性来“看”,二者都使文化现象的认识单面化了。实际上,文化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统合体:文化的表层现象只是其载体和外观,只是文化的储存器、显示器、转运站,只是文化存在与流转的物理空间,其主要功能是承载文化、表达文化;而文化的抽象实体只是文化的精神性印迹,它承担着在人心目中形成文化的“完型”、“意象”的功能,是文化的主观化形态。二者都不可能成为文化的具体与全部。只有经由“激活”(物质性文化背后的意象)或(将抽象化文化与其物质对应物关联起来的)“具体化”等环节,上述单面文化的真实形貌才可能显现出来。为此,一方面,我们既不能将文化等同于其承载物,因为“文化是文化主体和文化承载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性的关系性的存在,文化不仅取决于文化对象、资源,而且取决于文化活动的参与者”[3]。正如史密斯所言,“肉食不仅代表了肉食,它还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4]。只有透过文化实体的表面,我们才能把握住文化的潜在意蕴和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文化视为抽象实体,因为“文化不是一个单独或同质的实体,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5]。换言之,文化的抽象概念只是人们认识文化的一个桥梁,而非文化事物的本身。
(二)“去身体化”倾向
文化是属人的一种事象,但“属人”并不意味着文化属于人的观念、知识的积累或从属于人的行为行动,而是意味着它从属于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建构、塑造,身体是文化最丰富、最有效的表达手段;要知一种文化怎样,我们可以从栖居于这种文化中的人的身体表现来得知。科斯洛夫斯基指出:“行为者有身体表现的向度,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能力,失去了空间性的力量,即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6]可见,人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是人唯一在世的东西,身体的表现是文化创生的根源。与之相应,人的文化的独特性是人的身体的独特性,人的文化与其身体之间具有一一对应性;文化是人的身体的文化,人的身体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现实存在方式是人的身体及其表现,任何观念、行为的东西都必须经由人的身体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身体就没有文化,文化与身体具有一体性的关联,身体与文化之间相互阐释、相互依存、相互塑造。同时,也正是因为有文化的存在才使人的生理性构架成了身体(body)而非躯体(flesh)。进而言之,个体的身体即个体的文化,个体文化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构成了个体所归属的群体的文化。因此,在文化的认识中,无论是将之理解为“知识、观念、价值、规范”,还是理解为“意义、符号、象征”,都只能算是人的身体的延伸,是外在于身体的文化,而非对完整的身体实践(即在身体参与中生成的实践)的一种表达。文化的特质不仅仅在于它是观念世界、符号世界的一员,还在于它是沟通人的两①人是“环境人”,所有身体都占有一个空间并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个生活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两种实践(“话语中的实践”与“实践着的实践”[7])的纽带和背景。显然,在此只有身体才能完成这一重任。在这两个世界、两种实践中都离不开身体的在场和参与,相对而言,符号、象征、观念、价值都必须通过由身体演绎出来的行为变动或外观变化来实现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身体成为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是所有文化赖以寄存的大本营和整合中心。正如莫迪恩所言:“我的身体就是确定周围所有事物的参照点,我成为一个据点的圆圈———我的环境———的中心。”[8]换言之,文化源自身体、通过身体、影响身体、表达身体。只有立足于人的身体,并从人的身体在生活空间① 中发生变动的真实原因及意义出发,人的身体才会获得客观性和实在性。文化既非孤立存在于主观世界的文化,亦非孤立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文化,而是身体的文化,文化“属于人”的实质是属于人的身体;“世界不是在观察者的想象或组织之外存在”[9],而是在身体的实践中存在。离开了身体,文化无从体现自己、承载自己,势必导致文化意义的泛化。去身体的文化或无身体的文化就是无人的文化、异化的文化、迷茫的文化、虚无的文化,身体构造着文化定义的参照系,因此,对文化概念的调整和更新必须积极关注身体这个中心,以身体为基点来理解文化是未来文化研究的走势之一,福柯、罗蒂等人正是这一趋势的始作俑者。
(三)凝固化倾向
在文化理解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模式”、“惯例”、“结构”、“符号系统”等,似乎文化是有固定结构与形态的存在,是人的一种稳定的结构化生存方式。这就使活生生的文化被冻结了起来,成为一块僵硬的概念木乃伊。身体的本质在于生命,生命的存在构成着生活,生活的本性是流转和变迁,故身体就存在于流转的生活中,文化就存在于生活方式的创生中。因此,抽象的概念、呆板的结构和僵化的模式不可能冻结文化、捆缚文化。文化是一系列瞬间事件聚会的暂时社区,是“事件之流”,是一系列“经验机遇”。每一次经验的创生都是“体现了自我———决定或自我———创造,并因而对未来施加了某种创造性的影响”[10]276,都给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文化是新事件不断涌现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尽管有稳定的行为惯例、习俗传统的积淀,但这些惯例、传统都是“活”惯例、“活”传统,在它们中文化的“流”与“变”实现了统一和交融。正如格里芬等所言,“实在的基本单位不是持续的事物或实体,而是瞬间的事件”,“事件不是缺乏经验的‘空洞单位’,而是……‘经验机遇’”[10]276。同时,文化也不是各个文化要素的简单综合或静态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型构(formation),即解构与建构交替作用的过程;文化的存在绝非既有结构的恒在或机械复制,而是以结构化为潜流的持续生成过程。可见,文化即便是有结构,这种结构也是一种“建构中的结构”;文化即便是有形,这种“形”也是流变中的“形”;结构与“形”只是文化发展的趋势而非现实,是文化的一种瞬间状态而非恒在形态。可以这样说,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时间性的延绵,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是一种“创造性的进化”[11]。在此,那种将文化视之为“凝固结构”的看法只会使文化的发展丧失活力与生机。
(四)价值核心化倾向
价值偏好、价值航舵作为文化构成的中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文化的另一倾向,提升人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人掌控价值观的航舵,接受文化的价值引领。诸如,在上述理解中学者们认为,文化体系的顶端是“中心价值体系”(鲍曼),文化的分化是价值观的分化,文化的认同是价值观的认同,文化的标签是价值偏好的标签等,都是这种倾向的体现。在价值观标准的主导下,文化被人们区分为三类九等,不同文化形态之间有了优/劣、中心/边缘之分。可见,价值观把文化从其他事物中识别出来,使文化的其他因素集结在它的麾下,从而规范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价值轴心化的倾向也使文化成为一种人格化的存在,一种自觉化、意识化的存在。如认为“文化是外显扩大化的人格”(本尼迪克),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的终极指向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等[1]343,就是其集中体现。实际上,文化是一种半自觉性的存在,文化机体是有价值的存在和无价值的存在的统一体,价值只是在特定境遇中对文化事象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主观化反映。价值因素并非文化本体的东西,而是由文化本体在与特定主体相遇、发生关系时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功能属性。价值轴心化只会使文化陷入纯主观化和价值争端的漩涡,只会使文化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附庸,而非人实现其总体化、具体化发展的平台。人的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能借助身体的“文化化”转变来积淀人生活历程中的成功行动惯例,来自觉将心灵的灵光、思想“融”进身体,形成人的“实践意识”①,从而推动文化的稳步发展。因此,赵汀阳指出,“文化和生活的价值就在于它自身的健康状态”[12],强化文化所承载或认同的价值只会使之步入歧途。而且,价值偏好和倾向的力量对人的干预也非全能的,相反,人的价值选择也只是特定文化(如群体文化、特定行业或种族的文化等)建构的结果,人的价值意识“是由文化世界教化、建构、发展起来的”[13],而决定人价值选择的潜在偏好正是其所归属的文化系统。故此,文化先于价值而产生,文化是价值产生的背景,价值选择的不自由性显而易见。在许多情况下,人在文化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不自觉或“潜意识”的,价值核心化的文化倾向是值得存疑的。
(五)孤立化倾向
所谓“孤立化倾向”是指研究者在阐述文化时常常会表现出一味将文化拆解或分析为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或单位,如“特质”、“集体意会”、“知识观念”、“知识库”、“行为知识”等的倾向。对于这些理解,研究者尽管进行了一些综合,如概念形态的综合、载体形态的综合、逻辑结构维度的综合等,但这些综合大都是研究者在脑海中对文化进行结构化综合的结果,而非自然的、合乎文化事物自身逻辑的整合,即在现实文化形态中的具体化综合。文化的整合需要的是一种黏合剂,这种“黏合剂”不能靠人为的、专家的头脑来提供,只能在具体文化形态中去寻求,否则,研究者的综合就可能将文化内在的、本然的联系阉割掉,难免会将文化离析为一些支离破碎、互不关联的文化要素和概念单位,导致文化研究发生“走形”。我们认为,文化“多于其各个特质的总和”[14],对文化的整合要靠描述文化的整体“图景”来提供。这种图景是文化的天然黏合剂,它不仅包括了人赖以行动的惯例准则之“网”,还包括了象征意义之“网”,人就是这些“网”上的一个最具能动性的结点。文化图景决定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只能站在文化整体景观的立场上去看待人的身体及其行动,而不允许对之进行理性还原式的因素分析。可见,基于文化图景的整合是防止上述“学究化”整合和人为化的谬误,遏制孤立化的研究倾向的一剂良药,它能够引导研究者按照文化的本身样态去研究它。鲍曼指出:“文化不存在于被规范所调节的生活方式之中,而存在于区分、分开、分割、分类的持续冲动之中,即存在于通过不同的实践对新意义的联想中。”[15]可见,文化的分化、分割是自然的分化和分割,而非人为的、规范的分化和分割,对文化的分析必须以从文化图景中自然分化出来的单位为研究单位。
对当代文化概念的重构
针对上述不良倾向,我们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指人的生活样式,是以身体为载体、以生活为背景、以行为为外显的生活图景与生活图式构成的有机体。具体而言,该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具体内涵。
(一)文化是人的生活图景与生活图式有机统合而成的生活样式
从字面上来看,生活样式是“样”与“式”的复合,其中“样”就是生活的样子,“图景”就是对这种“样”子的一种全景式描绘,就是对人的生活景况的总览。由于人的生活景况、图景是以人的身体为中心,以人的身体所到之处的生活空间为场域的,所以,身体就是这一图景的总载体。这样,生活图景就是以身体为光标、以身体的移置①的轨迹(即行为)为画笔而勾画出来的一幅文化景观。生活图景是人的文化存在的整体状态,它与文化图景是同义词,是一个所指的两种指称。文化的图景是有边界的,身体的边界即文化图景的边界,身体是生活在文化图景之中的,是“在世之在”;人的身体在文化图景中的位置总是变动的,所以人的文化性不仅体现在人所特有的文化景观上,还体现在影响这种位置变动或行为轨迹的模式和范例中,这种模式或范例就是人的行为生成图式,即生活图式,文化图式即生活样式之“式”。就文化的图景与图式之间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对应性:文化图景有实景与虚景之分,实景是指那些由现实的惯例性秩序,如经验、习惯、传统、习俗和现实的思想活动(观念、理论等控制身体时产生的行为轨迹;虚景是指那些身体在虚在的象征世界,如人的身体所承载的衣饰、仪式、节日等象征物控制下所产生的图景。与之相应,文化图式也有两种形式,即行为逻辑的图式与意指实践的图式,亦称为行为逻辑与意指逻辑:前者是人在文化实景中的行为依据及行为生成格式,后者则是人在文化虚景(即象征文化)中的行为依据及行为生成格式。从动态的身体移置方式视角分析,文化图景是人在生活中所形成的自在的经验、习惯、传统、习俗与自为的观念、理论、制度等,与之相应的文化图式就是模仿、类比与创新、求异等。再从身体的文化虚景来看,文化图景是人的服饰、仪式、节日等“流露”出来的象征意义及“符码”①,与之相应的文化图式就是接受象征意义的召唤,遵循生活空间中的象征语法来行使。就二者间的差异而言,文化图景是从空间、静态、横断面维度来理解文化的一种方式,而文化图式则是从时间、过程、纵向维度来理解文化的一种方式,故文化是相对稳定与不断变迁的流动之物。
(二)身体是文化的载体
身体是唯一实存形态,而观念、精神、仪式等只是人身体的功能和延伸,文化的独特性来自人的身体的独特性。身体的此在性/有限性就是我作为个体的独一无二性:我不能转化为另一个身体,也不能由另一个身体转化而来,这个世界上注定只有一个“我”,因此,“我作为身体是不可重复的”[16]。当然,人与人相区别性不在于肉体意义上的躯体,而是文化“雕塑”、文化负载、文化构筑、文化标识出来的身体。所以,有人指出,“个性就是个人身上的习惯、习俗、爱好,人的根本差异铭刻在身体上”[17],身体的差异是人的文化的差异,身体的相似是文化的相似,身体的样子与移置方式就是文化图景与文化图式的缩影或翻版。一句话,人的所有文化都是人的身体的文化,而非观念的文化,相对于观念文化而言,身体文化具有先在性和本源性。身体标识自己存在的方式是给身体以各种妆饰和定位,前者如服饰、仪式、发型,后者如身体在特定时空(如仪式等)中存在的惯常性位置。同时,身体还通过自己在生活空间中的移置轨迹和行动依据来标识自己的存在。譬如,是按照惯例、习俗、传统而行动还是按照观念、理论、制度来行动,都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人对这一问题的抉择及回答方式都体现着人之身体独特的生活样式,研究者就必须从这些维度出发来对文化加以全面追溯和探究。
(三)生活是文化的背景和舞台
生活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活动,生活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文化世界在和生活的关联中生成意义。离开了生活,文化就没有了源泉和根本,文化也就无从存在和产生。文化的图景和图式就是要通过阐明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来帮助人理解其生活的独特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性就体现为他的生活图景、生活状态与生活方式、生活图式的独一无二性,故人的文化样式之间总是表现出诸多质的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是绝对的,文化才成为个人存在的标识。同时,生活是“活”的生活,生活的样式自然时刻处在变动之中,人的生活样式也时刻处在创生之中。随之,人的文化之间的质的差异和水平差异不断被扩大,人的个性进而不断彰显。所以,文化图景的描绘与文化图式的揭示都必须以生活空间为依据,以鲜活的生活过程为基准。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人完善自己的生活、更好地适应和筹划自己的生活这一目的的实现。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意义之源,也是一切文化研究的意义之源。
(四)行为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和展现方式
文化作为生活样式不能直接加以把握,只能通过一定的“眼光”来透视。透视总是需要以一定的对象为标本,身体不能作为直接的标本,包括身体在象征空间的意义② 也是如此,因为身体的象征意蕴必须通过它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与效应来体现和存在。而且,从静态的身体上“窥探”到的只是静态的意义,它对文化的创生与发展而言无所裨益。身体只有通过在现实生活空间中的移置方式来全面展示自己的文化,这种“移置”即人的行为。因此,行为是文化最生动的表达方式,只有凭依行为、洞察行为、聚焦行为,才能对人的文化图景、文化图式加以客观地探察。行为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最真切、最真实、最由衷的表达:行为与人的观念、价值之间可以不具有映射性或一一对应性,但人的文化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对应性却是绝对的,因为“个体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就怎样”[18],他的文化就怎样。因此,基于行为的文化才是人最真实的文化、最实在的文化。沿着身体去考察行为,沿着行为去考察文化,是文化研究最可靠的一条道路。同时,任何行为是惯性与创新的统一:为了寻求“方便”,人的行为总会表现出一定的重复性和惯常性;为了应对新事物、新事件和新问题的挑战,人的行为必然会表现出反常性和创造性。人的行为的两面性实现了其生活样式的“生产”与“再制”,实现了其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五)文化是由确定部件构成的有机体
这种“有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化的两个要素———文化图景与文化图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不可拆解性。二者的统合也非机械拼接的关系,而是一个自然的、以具体文化样态为媒介的结合,只有两者合二为一才是文化事象的完整机体。纵然在研究中需要对文化进行分析或拆解,但这种“拆解”也只是理论框架内部的拆解和研究者“头脑”中的拆解,而现实的文化并非可以被“拆解”开来。其二,两个文化要素间的关联是以身体为纽带的。无论是文化图景还是文化图式,都要通过身体来显现自己,都要靠身体来建构自己,身体是衔接两个文化要素的自然纽带。其三,生活是文化图景和文化图式的存在世界。文化图景和文化图式是对生活方式进行审视、观察的产物,是对生活进行分析、探究的工具,因此,生活是文化图景与文化图式生成的共同根源,是由二者构成的整体,生活就是二者的连通器。
本文作者:龙宝新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