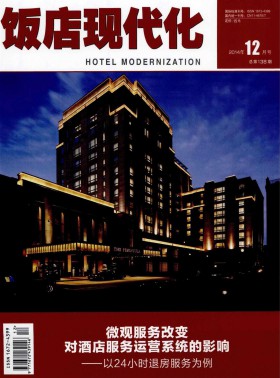作为19世纪70年代的一位留学生,辜鸿铭的西方文学背景(主要集中于西方古典语文)在他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四十年之后,胡适一代留学生的出现,首先在西方文学及思想文化的教育背景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辜鸿铭对于他那个时代西方思想文化话语的垄断。因此,辜鸿铭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两代留学生之间在语言、文学方面不同的观点主张与话语冲突。 一、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由文言、白话开始,自然地扩展到白话文学及新文学和新文化 运动上,并在新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以及实践途径方式等领域,表现出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的分歧乃至正面冲突。 辜鸿铭曾在一篇赴日演讲中[1],将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力量分为“旧中国党”、“新中国党”和“真中国党”。他将自己归属于由晚清“清流派”核心人物张之洞开宗的“真中国党”。如果按照这种划分,胡适的思想源流则应划归晚清由康、梁开宗的“新中国党”[2]。辜鸿铭的上述观点,是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并在语言文学变革之倡导与实践方面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的,不过其基本倾向,与其19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仍基本一致。 如果就其思想的某一侧面而言,至少到1913年底,胡适思想似仍可归于辜鸿铭所言“新中国党”一流。 胡适在留学之初,其思想中为中国辩护,包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辩护的成分依然明显存在,单不说他曾明确反对过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并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之判断,直至1912年底,他在日记中还曾提到自己有过一个著述计划,即《中国社会风俗真诠》,此计划书之英文书名,即“为中国社会习俗制度辩护”[3]。尽管在计划中的该书目录中,已经列有“中国之语言文字”和“新中国”章节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语言文字以及新中国,绝非后来胡适文学改良思想之主张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中国[4]。换言之,此时胡适思想中的中国意识与现代意识,大体上与康、梁所持思想立场相近[5],当然其中亦与辜鸿铭此间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立场有着某种相似性。不过,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这一时期胡适思想与辜鸿铭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是更深刻地反映出晚清“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之影响。同时亦更清晰地昭示出,胡适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高扬的思想主张,尤其是他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之主张,是如何超越“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的[6]。具体到语言文学而言,直到1914年初,胡适对于中国语言文学问题的思考,依然没有超出在旧有的框架下予以有限改善的个人处境[7]。无论是他在当年“一种实地实验之国文教授法”札记中所述,还是他后来在《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相关内容中所阐明,都还没有全面涉及到如后来新文学思想中以白话文为本体,以现代人和现代情感、现代思想、现代审美为基本立场的相关主张[8]。 胡适中国意识与因袭思想的“改变”,在留学时期经历的第一个明确的自觉,可以从1913年10月8日《道德观念之变迁》及10月9日《中国似中古欧洲》等则札记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得到证实。前者表明,胡适在上海时期的“进化论”思想,在道德领域或道德话题上有了进一步深入,而后者则初步显示出胡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之判断,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西方参照。 而上述思想自觉,或超越晚清“中体西用观”及“维新变法”主张在理论上的标志,就是胡适在1914年1月底数日札记中所罗列之思考,其中有《孔教问题》(1月23日)、《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1月25日)、《我所关心之问题》(1月25日)等。这些思考进一步从理论上,尤其是从思想文化的现实处境上,反映出他对中国当下思想文化之症结性困扰,已有了初步却渐趋清晰之认识。 这种具有鲜明胡适特色的“问题意识”,与他后来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倡的以“发现问题”作为现代思想之起点,以“再造文明”作为现代化运动之归结,以“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作为方法上变革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脉相承性。 而胡适思想的基本框架及整体性,至此亦初步彰显。 胡适的这种问题意识与变革思想,反过来又在语言文学层面得以具体实践落实,并最终扩展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全面的怀疑、反省与批判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性自觉”,恰恰反映出胡适式“自觉”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变革之思想理路之支点。其一是西方参照系的确立,无论是西方社会发展观及历史观之参照,还是西方道德价值观与审美观之参考;其二是对“中国式”思维方式本身的丰富完善。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胡适语言文学思想的批评者,往往只注意到胡适思想中的“西方参照体系”,并以此作为批评胡适“全盘西化”思想的依据,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胡适的变革思想或现代思想中,更具有超越性与思想意义和价值的第二种理路。简言之,即他所谓“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9]。也就是胡适倡导并实践了一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胡适进一步落实上述思想学说的努力,即关注“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以及天赋人权说之沿革”,已经明显与辜鸿铭的思路相异。 就公开发表的文章而言,所谓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或者辜鸿铭对于胡适及“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批评,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亦仅集中于两篇文章,即《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年7月5日)和《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年8月9日)[10]。值得注意的是,当辜鸿铭引述胡适的相关观点时,在提到“活文学”的同时,也提到了胡适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或者“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11]等。此亦足证,胡适、辜鸿铭之间的“分歧”,绝对不仅止于文言体文学与白话体文学之间的争论,而是“蔓延”到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所有相关话题上。表面上看,辜鸿铭集中攻击了胡适的文言为一种死语言,这种死语言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不可能用来表达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等观点。而其论述,却很快转移到了对于语言文学背后之道德内涵的讨论上。正如他抨击那些认为“文言不适合创造活文学”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时所言,这些人是“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12]。为此,辜鸿铭引证了西方文论者有关“诗歌需要讲求精神法则”,以及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具有传输生活之道的意义—文以载道”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由此说明,文学革命者的观点立场,既背离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亦不符合西方精英文学思想之正道:归国留学生们对于西方现代文论思想“断章取义”或“偏颇”之汲取,不仅注定了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文化是一种道德空洞化或自我矮化的思想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反高雅的粗鄙低俗的思想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辜鸿铭不仅偷换了胡适新文学思想中以“现代之道”取代“传统之道”的观点,亦对胡适思想的西方语境之“局限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亦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体系中道德原则的永恒性与现代意义和价值。#p#分页标题#e# 辜鸿铭对胡适的批判或对中国归国留学生们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之批判,所展开的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以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道德中心论,来反对现代留学生运动中变革中国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反激进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13],亦可在西方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二是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强调并坚持本土传统的独立价值与现代意义,对西方传统在现代的“迷失”与现代中国对于“迷失”了的西方的错误模仿与学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这种批评语境中,胡适以语言文学为起点的“充分的世界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与辜鸿铭所坚持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立场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二、胡适、辜鸿铭在对待中国现代文化—文明以及西方文化—文明的认知评价上的分歧,并不像辜鸿铭有些文章中所言那么简单。 与胡适从宣扬西方现代文化—文明开始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所不同的是,辜鸿铭在近现代思想领域的出场亮相,恰是以其犀利的对西方主义批判,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为标志的。与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路亦不同的是,辜鸿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图,恰在其强烈的非西方式现代化和反唯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于他对现代化和现代运动多元化多样性的坚持。 辜鸿铭思想的“保守性“,并非只是在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倡导者之论争中才彰现出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辜鸿铭对李鸿章式的洋务运动以及康梁变法主张的批评,尤其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犀利抨击等[14],已经反映出他有所保守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理论上大体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一致。 就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之关系而言,早在胡适归国之前,辜鸿铭就曾在致爱丁堡大学之校友、时任山东威海卫殖民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不无感伤地戏称自己为一个旧派人物(oldChinaschool),且在“现代青年中国人”[15]眼中根本无足轻重—辜鸿铭这里所谓“现代青年中国人”,在时间上还应该不包括胡适。 有意思的是,辜鸿铭对自己在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中地位“偏低”之感慨或抱怨,其实还不限于中国。就连在他的影响似乎更大的在华西方人社团群体中,他那些非西方主义的思想批评,亦难博得广泛喝彩。1916年8月6日,他在写给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就抱怨当时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编辑多年来忽略自己,对他所讲述的“中国的牛津运动”(ChineseOxfordMovement)甚至自己的相关著述,亦毫无兴趣或不屑一顾[16]。 由此展开,其实辜鸿铭的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批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仅限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思想文化,都处于一种“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因为这个文明时代偏离了甚至迷失了文化真正的原则标准。而为归国留学生们所影响下的现代教育,在辜鸿铭看来,亦走上了一条与真正的道德准则南辕北辙的道路。“就‘教育’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一个人越变得有文化和学问,他所受到的教育就越少,就越发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17]这里的所谓“教育”与“文化和学问”,当然不是他所坚持的古典教育和文化,而是他所批评排斥的现代教育和文化。 究竟如何认识辜鸿铭对西方思想文化之立场观点?辜鸿铭在其晚年《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演讲中,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解析,他驳斥了那些认为他是一个西方文明的笼统反对者的批评[18]: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声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确实值得称道。但就我之所见,欧美人使用高度发达的科技成果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是无法给予赞誉的。 他还说:“我认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文明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就像《圣经》里所记载的建造巴比伦塔的人一样。欧美人只顾将其文明一个劲地加高,而不顾其基础是否牢固。”[19]那么,辜鸿铭所说的“文明”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20],也就是他更常说的“道德标准”。这种作为“道”“体”的文明,被他视为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文明的最高标准:如果一种文明,没有或者忽略了对于这种基础的发展,没有去发展并维护它的道德标准,那么这种文明就失去了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明的基础。而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思想文化和现代学问,都不应该偏离甚至更紧地围绕着他所说的道德基础。一般而言,辜鸿铭并不反对“文化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一味排斥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但他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并不是专力于给人们带来多少物质性的享用,而是看是否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才是辜鸿铭所谈到的一种文化的经世致用。 对于文化的功用,尤其是涉及到现代文化及文明,包括作为现代文化及文明之“标志”的西方文化及文明,胡适的认知与态度都与辜鸿铭大相径庭。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自然地结出类似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明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及文明中,并不自然地包含着能够开拓出现代文化及文明的“因”。而这样的“因”,只能够由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自觉主动地“造”。 同为归国留学知识分子,辜鸿铭与胡适对如何去“造”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因”,在思路上亦大相径庭。除了他们在究竟何谓“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之正道方面理解的分歧之外,两人在文化与文明之价值判断、实现之方式方法等方面之分歧似尤为严重。究其原由,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皈依困扰乃辜鸿铭中国文化思想命题的起点,也是辜鸿铭现代文化思想中道德—价值中心论与中国—东方中心论之基础。辜鸿铭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历史处境与世界处境的认知,与他个人的中国文化认同与皈依之路基本上是同一的。#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虽然同为留学生,但胡适一代似乎并没有辜鸿铭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皈依之危机感与焦虑感。原因除了近代中国已经历过数十年之西学冲击,更关键的是,胡适留学时代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心与权威地位的体制性存在-科举考试制度业已废止。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从一种体制性的关系,转变为一种个体性的思想—文化处境与自我选择。与此同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分解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有效性、乏效性及无效性之争议。与上述争议相关的,就是如何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进一步明显提升。 留美时期的胡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恰恰体现出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改造的自我认知之路,也基本上符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的现代文化思想运动之基本路径。而辜鸿铭远离故国文化边缘的早年经历,以及异国教育之后的回归之旅,亦被他自己饱含民族道德,激情地确定为一次朝向正统的中华文化的回归之旅。 如何看待辜鸿铭在近代中国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与文化侵略中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述?如何看待他在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倡导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运动中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心主义? 如何看待他在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所倡导的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文学运动中所倡导的以文言文为中心的贵族精英文学—文化?似可这样认为,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核心,可以简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以本土儒家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反抗西方文学—文化侵略与话语霸权;二是以中西方人文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的反抗以西方近代科技主义和物质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文明主潮以及这种主潮在中国的蔓延。而这种非西方主义或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主张,尽管彰显了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难以平等共存的现实窘境,亦折射出所谓文明多样性与多元化之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与文明冲突中的实际状况。 三、作为胡适、辜鸿铭思想文化分歧的一个现实归结,在二人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的一个疑问,就是辜鸿铭最终离开北京大学,其背后有否胡适的因素。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所谓的“胡适因素”,究竟是一种当事人个人不断强化的心理感受,还是一种现实的干涉力量或话语权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区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所扮演角色和所承担责任的关键。 胡适与辜鸿铭之争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现实话题,就是辜鸿铭“被迫”离开虽然倡言“兼容并包”,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21]。这是否与胡适的背后或底下干预存在关联?换言之,胡适是否将两人甚至两代“海归”之间的思想主张之分歧,延伸到了本属于思想学术以外之范畴?有关辜鸿铭离开北大之原因,已有不少讨论[22]。但无论是胡适应为辜鸿铭之离开北大承担一定责任的说法,还是不应过分解读两人之间的分歧及辜鸿铭离开北大过程中“胡适因素”的说法,都不能提供有关胡适在这一行为中所实际扮演角色之铁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到1920年间,胡适与他的另一位新文学对手梅光迪之间,就征询后者是否可来北大担任英文教授的往还书信,似可作为当时胡适确实考虑过找人替换辜鸿铭的旁证材料,并多少有助于认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可能扮演的“幕后”角色。 梅光迪在1918年7月2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曾就来信中所询归国后就职计划及赴京来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诸事一一奉答[23]:适之足下:前日由叔永转来手书一纸,谢谢。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想。至于明夏归去,亦不能即担教授之职,须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始可言就事。然亦决不作入京之想矣。 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流,以冒称人道主义派。在今世西洋最合时宜———popular&fashionable———故云。毫无分别,眼光如是。西洋文学界近百年来如英之维利多亚(应为“维多利亚”———作者)时代数人,总之,葛脱美之爱谋孙外,皆白桧以下,何足道者。吾料十年廿年以后,须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遇之矣。草此即问起居弟迪上七月廿四日从信中可知,一,梅光迪初计划于1918年夏季回国,但对于归国之后的工作安排,却让人多少有些费解:先要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照理说,留学生归国,急于落实之事莫不如此:回乡省亲;完婚(如果出国前或留学期间父母已有命且已订婚的话);落实工作。而梅光迪无需像不少留学生那样,回国后急于奉命“完婚”,因为他出国之前已经与邻村女子王葆爱成婚。更何况从他后来回国后写给胡适、张慰慈(祖训)的信看,梅光迪回国之际欠了不少债务,应该说是急需工作来偿还欠款的。但他上述信中那种悠哉游哉、一身轻松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不明就里。二,对于胡适来信中询问能否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事,梅光迪亦断然拒绝,所言理由有二,其一是不会按照原计划于1918年夏天回国,其二是即便按原计划回国,亦没有到北京高校任教的打算。至于为什么如此不愿“入京”,信中未曾言明,猜想不过是对胡适因新文学主张而“暴得大名”之忿忿不平。 参照《吴宓日记》记载,梅光迪于1919年10月离美返国,且临行前为旅费事确实欠了一些债务。“梅君迪生将首途归国,赴南开学校英文教员任。频行数日,为助足旅费,琐务碌碌。十月四日晚,共诸知友,会于陈君寅恪室中,而亦未及谈志业之正事”;又10月5日日记云:“星期。晨,偕锡予为梅君运箱搬箧。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四时半,送至南车站,握手而别”。不过,胡适、梅光迪之间,显然并没有因为梅拒绝赴北大任教而就此中断联系,相关话题亦未就此终止。#p#分页标题#e# 正如前言,梅光迪回国之初,经济上颇为窘困,无奈之下,只得向远在北京的老同学胡适、张慰慈借款。梅的“呼救”,显然得到了胡、张二人的及时“搭救”。在1920年6月寄自天津的一封信中,梅光迪这样写道[24]:适之慰慈两足下:借款汇票已收到,谢谢。因近甚忙,至昨日始到银行取款。未取款前,弟恐有周转不便之处(弟前闻天津各银行对于汇票取款之人种种为难),故须俟取款到手后始敢覆书鸣谢。不料昨日在银行中毫无为难之处。愚弱书生缺乏商业经验,遇事易生恐慌如弟者,殊可笑也。 北大英文藏书多否?弟欲多阅于十九世纪文学书籍,以资参考。若尊处能助力,当于大考后来京小住。 草此即请起居弟光迪启六月四日这封短信表明:归国之后尚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的梅光迪,与胡适之间尚能如此亲密无间地书信往来,而且也坦然在胡适面前显露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梅光迪的这种“示弱”,与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坚持甚至固执相比,实在有值得关注之处。不过,梅光迪并不愿意自己这种主动“示弱”被理解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生活上的“失败者”,更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示弱”,被放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学术上的“示弱”。对此,梅光迪在与胡适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无论他的现实处境如何不堪。 不过,这封短信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梅光迪提到希望在学校期末开始后的暑假中,能来北大查阅英文资料。仅就此言,梅、胡之间在1920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梅光迪这里,亦期待继续发展两人之间的学术交谊,毕竟那是读书人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而早在3个月前,在另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将去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事介绍得更为详细[25]:适之足下:数日之谈,总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从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 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spiritof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焉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今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主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凡以上所言,不过兴来偶一提及,非与足下挑战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尤须不期速成,不从多数,故弟之不服,欲与足下作战者以此。若足下以为一学说之兴,能风行一时,即可称其成功,不反对者之崛起,则误矣。 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焉。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为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若来京,则须授课五六时,否则往返时间费用得不偿失。弟所愿授课者为GeneralPrincipleofLit-eratureorIntroductiontoLiterature;GreatEnglishProseWritingofthe19thCentury;Ad-vancedComposition;TheTeachingsoftheNo-vel等课。若能授两门,则须早日商决,俾弟能从事预备,且可向凡善堂购书,望足下速行示知。 弟此即问起居慰慈处望代通候。 弟光迪三月二日显然,从两年前梅光迪尚在哈佛期间询问起,一直到1920年初,胡适似一直有意邀请梅光迪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而且以胡适当时在北大之影响力,包括当时正担任英文科主任,亦足以促成梅光迪的北上,当然前提是胡适愿意这样做。至于为什么最终梅光迪没有北上,却选择了南下———到南京高师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其中原由,总不出梅光迪的性格,以及与胡适实在难以走到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并肩作战等。而梅光迪1920年3、6月间两次去信查问是否可来北大任教,却未见胡适明确答复,似可说明,胡适确实曾有过找人替换辜鸿铭教职的念头,而胡适就梅光迪是否可就北京大学英文教授之征询往来两年,恰为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由语言文学之争发端的矛盾冲突逐步激化之时。而最终辜鸿铭离去而梅光迪亦未来成北大,则至少说明,胡适并没有将自己最初的一念,在梅光迪身上转换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辜鸿铭、胡适围绕着文言、白话所展开的这场争论,其实不过是一场并没有真正展开并各自得到充分发挥的“笔战”。其中当然与不少意气因素有关,但他们所代表的两代留学生在解读、理解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精神实质上的“差距”,却是明显不过的。这既与他们所接受到的那些具体的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信息、知识及学术训练有关,亦与他们所关注的所处时代的“中国问题”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对各自时代“中国问题”的归结与探究,反过来影响乃至成就了他们各自对西方文学与西方精神文化之路径与方法的把握,包括他们各自在中西文学与思想文化对话交流中所达到的境界及其成就。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议”与“冲突”,亦可以说丰富、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阶层对中与西、古与今等时代命题的认识与思考,在某些方面亦深化了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认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