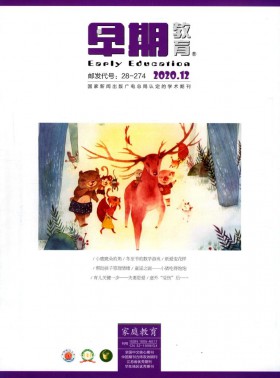江西,它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的功成之所。但是江西苏维埃运动是革命承转的最重要一环。早期江西的革命活动,在人员构成、经费和组织纪律性方面与革命的需要也相距甚远。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早期江西社会缺乏革命因子。历史事实表明,转入赣南、闽西的革命活动,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中国苏维埃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通过对中共早期江西革命组织生态的分析,可以再现中共党人在革命动员中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一、乡村未动:中央苏区早期的革命情形 早在建党之初,长江中游的赣鄱大地就显示出不是革命的首选之地。中共意识到“南昌青年团麻木不仁的居多,我们现在除了设法使他们渐渐地发生觉悟和感觉到社会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别的什么重大的责任都不希望他们现在去担负。”[1](P14)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时,青年学生的斗争激情也是很明显的。如1925年成立的江西高校毕业考试委员会,当年未见实行,到1926年春,主管部门则通令各校,凡当年各校之举行毕业者,须受该会严格之试验,试题由该会代出,各校须将一年内所受之课程先行报去,试验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一举措与赣地团员学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地学生纷纷起来表示不满,正所谓“南地学生素向沉寂,各种政治社会运动,都很难引起其加入,惟关于此种切身利益的考试问题,则甚为注意。”[1](P415)总之,“江西是小农经济社会,在北伐军未入赣以前,党的组织不过是一研究式的团体,纯以感情结合,多系知识分子。”[2](P158)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革命的积极性。 1926年10月1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江浙区各地代表会议,讨论暴动计划,陈独秀致训令于各省于1927年党的五大之前增加党员数计划,最高的是两广10000人,其次为江浙和湖南为7000人,江西是2000人,而福建与安徽是500人,仅多于云贵(200人)[3](P78-79)。由此可以看出,江西并不是革命的首选之地。有关江西的革命情形,1959年在接受江西省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4](P52)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对于农民运动也是迟迟不能走向正轨。革命分子赵醒侬在九江游庐山,附带调查脚夫工会情形,旨在发动当地百姓起来革命,结果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在报告中不得不说:“庐山脚夫大半是附近农夫,夏天抬轿和挑担,其余的时间都是回家种田去了,并且生活费甚低,每日进款夏秋间很丰,他们并不想团结,勉强去组织他们是徒劳无益。”[1](P16)农民的生活状况与革命积极性可想而知。而对农民的散漫、很难组织起来的情形,时任吉安特支书记的郭化非则说:“(农民)住居散漫,工作时间太多,日间差不多没有一时休息,夜间又睡眠得早,因之,宣传与训练很难接受。我们到他们的作业场中(菜园)去演说,聆者很少,每次至多不过10余人”[1](P272)。 九江地处长江口岸多脚夫、搬运,被中共认为是搞工运的理想城市,但同样是让革命党人一筹莫展。中共党人道,“这次日清码头工人大罢工,办理算是有点秩序,结果仍归失败,其中的缺点,不外乎没有相当的训练。九江这个码头,××称通商的口岸。其实学界与商界,都顽固得很,你就叫破了喉咙,想他们出来援助,也是不行的。他们抱定了宗旨,不问外面的是和非。”[1](P100-101)这主要是因为在江西的很多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如在江西修水,中共所依靠的农村工人诸如“手工业工人如缝工、铁匠、木匠,隋性特别比他处不同(如工作时间每天不过八小时,每人做衣一件还做不成,须要工钱五角吃主人的饭……)职工运动,殊毫无效。”[6](P89)面对中共党人的革命主张,市民们也只说:“他们的主张固然好,但是如何得成功。”[7](P204) 江西这种“落后”的革命情形在党的相关文件中也多次提到。1927年11月30日,在《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提到:“中央负责同志大都认为目前江西革命是没有多大办法与希望的,因为江西民众非常沉闷,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讯及其他决议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料想与中央对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视。”[8](P44)在1929年12月12日的《江西省委报告》中再次说到“江西过去为一般人所轻视,认为在革命战线上是永久落伍的省份。”[8](P56)特别是在“文化落后的赣南,一般人的政治意识都是异常浅薄,同时党的工作,又只刚复开始,故党的政治宣传,不但未能深入群众,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因此,我们要使赣南民众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很坚决的要求,非特别加紧目前的政治宣传与煽动不可。”[8](P32)赣南革命形势的落后,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早期在江西革命的线路一再强调是“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9](P461)的北上线路。而且对朱毛红军“擅自”向赣南方向活动的行为一再提出严厉的批评。如在1928年10月2日的《中央致江西省信》和1928年11月6日的《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中都先后重申:“关于四军的活动范围,中央历次决定须在赣西和湘南,往赣南实为死路”[10](P3)、“向赣南去的战略,中央坚决反对,因为赣南群众与党的基础都非常薄弱。”[10](P394) 二、组织乏力:中央苏区的早期革命生态 1.革命同志的数量、社会构成与活动情形 中共革命初期的经验让革命者认为,想求革命的信念能为多数农民所了解,除了在学生中努力制造宣传人才外,没有更好的方法。这首先是因为在革命群体中,学生、知识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如1923年南昌地方团员共21人,其中“学生团员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潜、刘五郎、汪群、陈之琦、王朝瑾、汪伟、曾弘毅、何桢、、崔豪;小学教师2人:刘修竹、刘拜农;商伙5人:陈日光、周一尘、易虚、赵醒农、赵履和;工人1人:郭炳生;女子1人:许若兰。”[1](P6)这种知识分子团员的成分是越来越加大了,到1925年8月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南昌地委团员总数是52人(女3人),其中“工一,学四(十)九,店员二。”[1](P184)到1925年11月,总数55人,其中“工人一人,农人一人,妇女五人,店员一人,学生四十六人,教员一人。”[1](P243)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团员数增加了3人,但仍然是学生占了绝大部分。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统计全国党员是11257人左右,而江西只有区区105人[11](P84)。到本年度底,直属中央党部的江西党员人数也是在500人上下。#p#分页标题#e# 从上面的粗略的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见江西党部的组织现象之一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农民参与之上,各级指导机关还多是知识分子支撑着。同时,党的同志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非常的脆弱,从党的同志来说,“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当地政治状况,不知如何计划进行,党与群众几乎尚无关系。”[11](P86)1926年底,江西农运同志不下30余人,在北伐未到江西之前,有县农会7个,区会28个,乡会120个,会员6172人,但很少有党员同志在内,完全是农民自动的起来[11](P144)。而另一方面又是发展革命同志的窘迫,从当时的九江领导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试探性的提出来:“从前我们吸收同志是很紧的,现在采取宽点的办法,只要不怕的人就拉进来,不晓得有什么妨碍不?”[1](P259)另外,这种党组织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到后来江西省委还是指出:“(九江)县委要想办法打入群众中去,尽可能的找到职业,省委不是要你们放弃工作去自己找饭碗,而是要你们找得职业使工作更深入群众,这自然不是一天二天做得到的,但是要你们坚决朝着这个方向走,至少要做到半数县委不领党的生活费,这自然不是单为着节省经济起见。”[7](P183)1927年2月23日,《在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的会务总报告》中,江西省农民协会总共不下三十万,所列的15个县的农民协会会员数中,赣南仅兴国有1500人[12](P62),是最少的一个。 鉴于以上情形,中央要求江西省委也是:“应毫不顾的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拿几天的政权就拿几天的政权。”[13](P9)在赣南,党组织状况更是不如人意。1928年1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王××作《关于江西组织的谈话》,“报告1928年1月江西全省的党员情况:共有党员的4000人左右,……全省各县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为:南康临时县委30人;崇义特支10人;信丰特支5人;于都临时县委30人;赣州临时县委68人;兴国特支10人。”[13](P31)赣南总共153人,仅占全省的3.8%,而赣西地区党员在3000人左右。而且,赣南地区的党组织还经常受到国民党的破坏。如1928年3月,中共赣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县委机关被国民党驻赣州的独立第七师破坏。包括赣南特委书记曾延生和前赣西南特委书记宛希俨在内的12人被捕牺牲。同年,寻乌暴动领导人刘维锷、潘丽牺牲。1929年1月,赣南特委书记汪群被害于赣州城内卫府里。就是在1932年底,党的同志还向中央提出:“此地动员工作在粉碎防御路线,情形异常差,党团以及群众完全太平保守,没有特别紧张和以前不同……”[1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初,江西特别是赣南,革命同志中党员数量之少,构成成分单一,革命能力非常有限,是其革命深入发展的主要困境所在。 2.党的经费情况 当时革命经费的短缺,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 一是连开会的旅费都没有。在1924年中共文件中写道:“代英先生:开会日期究定何时?祈速告知。此间代表已选定赵君与毅君2人,赵因事多不能出席,将由毅君补充。但毅君旅费无着,非中局鼎力接济恐万难如愿,此事务望中局设法,并祈早给一个答复。”[1](P46) 二是宣传费用的短缺。在1924年5月31日《易虚、曾宪明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江西革命同志总结道:“我们预料这次工潮,可以扩大,因公司方面愈强硬,我们愈好宣传。不过我们有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那恶毒的金钱,没有这东西,宣传的工夫,实在的不大好做,因为口头上的宣传,是我们应尽的天职,重要的还是文字宣传。”[1](P92-93)1925年,“五•九游行,尤为困难,各校除给假一天别无表示,提议游行多说不可,且势所不能,末了,我们组织讲演团一队各处讲演,因经济关系连传单特刊等,都不能印发。”[1](P155) 三是办公费用紧缺,甚至加入组织的入校表也没有。就拿“首举义旗”的江西省万安县来说,“经济又是一个困难问题,连纸笔的小需用办公费都可说是没有一文,一些小的费用都由个人负责借,那里借得到呢?区委要县委津贴办公费的信……大概没有一信不加以讨论,这个问题终是无法解决,党费是收点,通告也不知寄了多少,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7](P212)本来是要自己印刷的传单,由于没有费用也只能指望上级邮寄二三十份来。 四是革命负责同志生活费用的缺乏。对此,九江当时的负责人坦言:“谈起内部训练,就要牵连钱的问题,因为教育工作做不好,固然有的地方可以说是负责同学缺乏指导,然而连开会也找不着地方,到购买新的出版物也没有半个钱,同学———尤其负责同学,差不多天天在谈生活问题,这样,叫怎样去教育他们?所以我在此地要附带申明,要想浔校内部工作做得好,第一便要最少给养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费,关于此点,还望总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1](P348)种种迹象表明,捉襟见肘的经费,严重地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壮大。 此外是党费收缴困难。如在九江“名义上有5个支部,同志有30余人,不能开会,缴费谈不到,如要则以为剥削他们,他说:‘我不向你要已经好,你还要剥削我吗?’”[7](P75) 几个月不缴纳党费,无故不到会的在不少的支部都是存在的。同志散漫,不肯到白色区域和红军中去工作,泄露秘密,讨厌开会,不交党费,就连支部书记也认为:“党费只是财政上的关系,忘记收党费的责任”[15](P205)。以致组织决议案中特别强调:“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和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体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16](P271)举步维艰的党费收缴工作,不仅减少了党的活动经费,而且充分体现了党的组织、渗透能力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又是“出钱买同志××罢工之错误”[7](P248)的不正确的发动群众行为时有发生,这一切使得江西革命迟迟没有走向正轨。#p#分页标题#e# 3.组织生活、组织纪律与上下级联系 当时的革命活动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铁的纪律性”。一是表现为党员的退出与加入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严谨。比如吉安小学教师彭世璞在1925年8月,因“革命是一个危及生命、妨害生活的活动”而自请退出,而在1926年1月,梁舜花、郭化非又重新介绍其入校,美其名曰:“同学彭世璞前因课务甚繁,而无余力从事本校工作,自请退学,本支校即行准许,现已卸减课务,在可能的范围内的本校工作已能相当的担任,今梁舜花、郭化非二同志特介绍他复入本校,本支校干事会已经准许。特此报告总校,请即备案。”[1](P338)据当时的中共党人李一氓回忆:“脱党的情况在武汉极为明显。(1928年)8月初,武汉国民党颁布了《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其中第三项就规定:‘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因为登脱党声明的人多了,以致汉口《中央日报》还专门登一个启事说:‘奉中央命令,关于党报登载脱离共产党或声明非共产主义启事,非经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审查盖章,不得登载。因此,本报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项手续的启事,一概不代刊登。’这种启事报上天天都有,少则一两人,多则10来人。启事的格式大概是这样:(一)我曾误入CY,旋因该团不合国情,已于四月间脱离关系,特此声明。(二)敝人曾经由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政见不合,早已退出,特此声明。(三)我以前被人引诱加入共产党,我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主义。”[17](P28)党员的加入与退出的随意性,表现了革命初期的组织纪律性并不如人意。 二是党的凝聚力与执行力非常有限。一直到1928年,党组织还是非常松散。在党的综合性报告中,更是指出“全江西的支部没有一个是能战斗的组织,是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这话并不过火,但看支部对党的工作党的政策执行结果,便可充分证明。每项工作执行的成绩,结果不能实现原所规定的十分之一二,有时竟至完全不执行,此外如不能按时开会,每个党员不能积极作工作,这种现象,也是江西工作严重的大缺点。”[18](P5)甚至有些党员则“纷纷请求特委调任地方党部工作,甚至以不调则自由行动来要侠(挟)。”[19](P182) 与此同时,党、团组织的运作更多是靠私人的感情来维系。这种现象的出现在革命伊始也是在所难免的。如1928年派人去安福开展工作,“历经9个月,但所派的是异地的同志,找不着本地人,因此,工作非常困难。”[18](P78)而相比之下,在江西的另一个地方的民众因有多数师老(当地人对文化人的一种称呼)革命所以也跟革命,并且分配工作时,又是以某人在某地能取得民众信仰,就分配他去某地活动,因此各地工农为着感情的关系,虽然对于革命的内容不明白,也就又(由)绅士说话加入农民协会。这种家长式的领导和亲朋好友式的动员,既是一种必然,也显示出革命得以深入的障碍所在。 事实上,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团体相同,早期中共内部亦呈现出“思想的复杂性”与“组织上的松散性”。一方面,早期的党员多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入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的党员多是富有浪漫性的年轻学生,因此,欲求当时的中共成为有纪律、有组织、能耐久的团体,显然不易做到。民众对党的组织纪律、党费收缴和上下级关系是非常粗放、感性而又各取所需的。 三、身份认同与革命动员:中共党人的应对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下此定论:如此“糟糕”的革命生态条件根本不适合革命活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霍夫海因茨在其《中共成功的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45》[20]一文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一般人所着眼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如农村的土地制度,佃户在农村中的比例,地方现代化的程度,农民民族主义的高涨,都不能单独的解释或者说从整体上说明共产党在整个中国各个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区的成功或失败。也就是说,在结构性条件和中共成败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他所得的结论是共产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人本身的行为。在这里,他所指的“行为”包含着一系列的概念,例如,革命运动本身的可行性和生命力,革命组织发展的内在过程,人员的素质构成,以及吸收新成员的严格程度。这一研究模式对我们如何分析赣南、闽西革命的兴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这种身份的认同就是来源于革命分子“消解”在民众之中。在赣西南的东固,“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第二天到东固所见亦如此。在此之前,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然而红四军三千余人一到就有军需供给,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经常有人送东西来,我们住了六七天,没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较好。”[21](P133)在宁都,苏区老革命同志张元标回忆:“1927年这里就开始了革命,当时有一个叫郭庭远的同志受湖南省委的派遣,来到宁都。后来由宁都县中学校长赖奎轩(高田人)介绍,到我们这里来。名义上是教书,实际上是开展革命工作的。郭庭远同志不仅会教书,而且会做郎中(医生),又会种田,很受老百姓的尊敬。”[22](P284)1928年2月,以教书为名到宁都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赖金声,“原姓邹,因赖姓为当地大姓,为工作方便改姓赖”[23](P25)。1928年春,“闽西特委派李天富、罗化成两同志来到才溪组织秘密农会。他们以算命测字的职业作掩护,秘密地作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他们白天穿长袍子装做算命的人,到处去给人算命测字,晚上就聚集工农群众在祠堂、庙宇内,有时也在山岗上的森林内或没人住的房屋里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秘密农会,吸收个别先进可靠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24](P4)1929年的龙岩县各乡小学教员,一般都是共产党员,白天教小孩,晚上办夜校教成年农民,夜学又设拳术馆练武,夜校学生差不多都是秘密农会的会员[25](P64)。1929年,“赖振标同志以做裁缝为掩护,从信丰县进入全南的社迳、炉迳、白石下一带,组织过农民武装暴动”[26](P2),旨在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广东接壤的“三南”地区。1930年,安远的茶梓暴动之后,以卖布为掩护的陈林和“信丰暴动失败后,到晓龙教书的共产党员曹天谷,”相继在信丰的晓龙,进行革命活动[27](P2)。#p#分页标题#e# 革命分子以一种农民可以接受的职业方式走进了农民的生活,同时革命的理念也就潜移默化渗透至农民的心田。中共党人教唱的山歌是“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鬼子来烧楼;旧楼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盖新楼。”[28](P26)龙岩后田暴动的第一个春节,夜校的学员主动地为贫苦农民写革命春联:“欠租久债用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28](P38) 总之,走向乡村的中共党人首先赢得农民的认同,有耐心、有步骤地进行其革命活动。据回忆,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29](P46)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情况。有一天,他和一位乡苏维埃主席通过一条田间小道到另一个村庄去,迎面走来一位挑担子的老?。田埂太窄,无法相让。他一边和老?打招呼,一边毫不犹豫走下田埂边的水田里,脚上的鞋没有脱,裤脚也没有挽。年轻的乡苏维埃主席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鞋也不脱就下了水?他认真地回答:“你看他的担子多沉重,不能叫他等着,更不能叫他让。旧社会当官的出来要鸣锣开道,老百姓得规规矩矩让他们。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群众中间工作,不让他,不就变成官僚主义了嘛!”[30](P302-303)从中可以看出,适应农民生活,从民众角度考虑事情,让他们获得了身份认同。而职业的俗化与多样化,更为增进了其与民众的交流。 从生活处境来说,贫穷不是革命惟一要素或者说贫穷不是就必然导致革命。赣南、闽西的民众相比其它地区并不是更为困苦,甚至有的地方还较为安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不存在革命动力,关键是,这种潜在的力量能否被调动、激起与发挥。四一二国共分途之后,中共别无选择地走向赣南、闽西的乡村,不多时日,形势有所改观:“1930年3月1日,红军在江西发展强大,鲁涤平等向叫苦,江西贵溪县长电称:‘属县匪共猖獗,靖卫队迭次失利。’……3月14日,鲁涤平电,谓:‘兴国失陷,赣城危在旦夕’。3月15日,红军围攻赣州。刘峙电,谓‘查赣西各县,十陷五六,迁延时日,中毒益深,舍今不救,后将不治,以全局言,阎冯勾结,暗谋不轨,固有燃眉之急,而赣省匪共日加蔓延,权衡援急,拟恳并愿兼筹,增调得力部队,统一指挥,责成认真痛剿,以安内外。’”[31](P77-78) 毫无疑问,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央苏区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尤其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坚忍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凭借着中共的这些特质,可以说无论是“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32](P2)的江西瑞金,还是在“商贾乐于市,耕者有其田”[33](P128)的龙岩附城,革命之火终究在苏区熊熊燃烧。总之,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中共党人的革命也只能是一场“书斋里的革命”;而没有革命者那种坚韧不拨、愈挫愈强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深入、不怕牺牲、灵活多样的革命策略与行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也难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