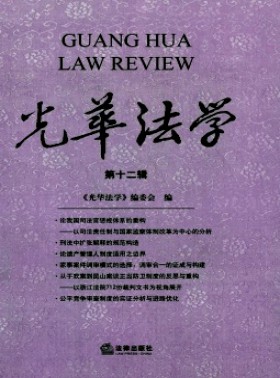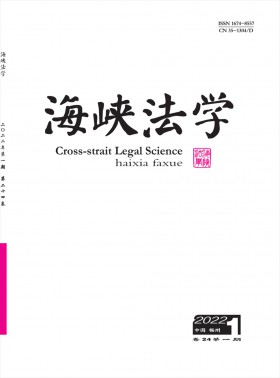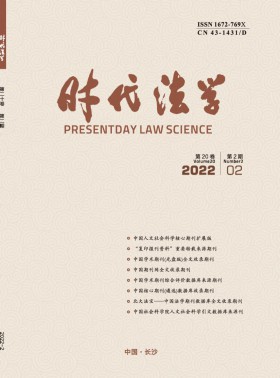一、我国传统法学的渊源、背景及其历史性检验分析 没有现代化的法学理论指导,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法律实践、发挥以法治国的极大功能。这一命题还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肯定,但已为近年来大量法律实践的事实所证明。实践中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文代法,有法不依等现象,以及法律的人民主权远未树立,“以法治国”未能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一样立为国策等,其思想认识根源在于未能实现法学理论观念的现代转变与更新。其中关键又在于把我国传统法学(指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进来的维辛斯基法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法学,苦苦坚持,以致在法律教科书上写的、“普法”课上讲的、书店里卖的、法学报刊上发表的、法学殿堂里传授的,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进来的那套理论观念:即法起源于阶级斗争的不可训和‘起源论),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本质论),法是阶级斗争或阶级统治的工具(功能论),法与阶级共存亡(发展论),法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特征论)等五条大纲。至于原始社会没有法、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以及惠新宋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有环保法、森林法等社会规范也“不是法”等,则是这五条纲领性理论的必然推理。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传统法学的渊源,它原原本本地载在维辛斯基著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之中。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套理论的产生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它适应于苏联当时高度集权的产品型经济,意志型经济,在政治上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科学上批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巨著,它是这一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它的很多东西是附加给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体现单一“统治阶级意志”,实行所谓“阶级统治,的人治型理论。远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义。 在苏联这套法学理论与“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相互配合,作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统治苏联政法界以至社会达半个多世纪,至现在问题才充分暴露出来。在我国这一理论对让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危害也已为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一)在“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阶级斗争工具”相互配合的理论指导下,50年代末法律、法学本身几乎也受到否定。法学刊物停出,法律学校停办,法学研究机构波撤销,公开不要“法治”而施行人治,法学与社会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挫折。在这一过程中,法学理论对社会建设实际上是起了帮倒忙的破坏作用。 这是解放后这种法学理论经受社会实践的第一次严峻检验。 (二)60年代初虽然开始重视法律,在方法上也作了一些纠正,但仍未提高到政治法律的根本理论上来认识,于是在同样的政法理论指导下,发展至“”的十年动乱,使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元勋横遭迫害,大批冤假错案祸及不知多少人民群众,国家经济建设濒临破产边缘。这是传统法学理论解放以来经受社会实践的第二次严峻检验。 (三)粉碎“”以后,人心思法,人心思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批判了高度集权的“意志型”、“产品型”经济模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开放、改革,使经济建设获得空前的繁荣,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法学理论观念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的。于是理论及实践严重冲突,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法学理论却要坚持“阶级统治”。当前,法制建设日趋完备,而法治状况却远不能令人满意,与这种理论观念未能转变有极大关系。’己束缚了人们的民主思想意识,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国家能否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的法学能否科学化、现代化起来,应该说,我国法学当前又面临着社会实践的第三次检验。 二、对坚持维辛斯基法学的种种“理由”的批驳 维辛斯基法学的核心是阶级论,即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和阶级统治(工具)论。 坚持维辛斯基法学的同志以种种“理由”为这种理论辩护,阻碍法学理论的创新与现代化。这些理由,从新近发表的论著来看,主要的有: (一)马克思早期言论的未“成熟”论。我在《论法学现代化与法的本质概念的科学表述》(《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中,引用马克思1842年投入社会实践以后说的法律“应是人的社会行为必备规律”、“应是人民意志的表现”、维护剥削阶级特殊利益的法律是统治的剥削阶级意志的表现等,指出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是系统论的,而不是统治阶级意志单一因素的质点论的。它具有多层次的系统结构,深层次是客观规律性、科学性,其次是社会性、人民性,再次则是阶级性(包括革命的阶级性和反动的阶级性),法律的阶级性随着社会发展至阶级社会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但它的科学住、规律性、人民性、社会性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而更加完善。相对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对不同论战对象的需要,马克忍、恩格斯等有时强调法的本质的某一方面,这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但是,在学习他们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时,务必系统地、全面地掌握,而不可固执于某一方面仓例如统治阶级意志性),甚至将之僵化起来,并将之运用于任何条件下的社会实践。 有的同志不同意以上分析,认为马克思早期说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性、人民性等话时还未“成熟”,应以《共产党宣言》上说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为“依据,而不应是马克思早期关于法的那些言论”为准,否则就是以早期的马克思的言论来否定经已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详见孙国华《也谈法学的现代化与法的概念的科学表述—与吴世宦同志商榷》、《政法论坛》1985年第6期)。笔者认为,这种成熟不成熟论、早期与晚期机械割裂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宣言》(1847年)发表以后的第三年(1849年)马克思还说,法律“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恩选集》第6卷第229页)而不只限于“统治阶级意志”的单一表述。#p#分页标题#e# 以《共产党宣言》来划分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这时应是更成熟了吧?里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形,1882至1884年中所大量论述的,由人民行使主权的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又惯法、继承法等已是白纸黑字,有目共睹的。难道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三十六、七年以后,马克巴连局恩格斯反而又都不“成熟”了吗?!这一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白应以社会实践为唯一的检验标准,而不应由什么人来一锤定音。 (二)目击为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大量论i正的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习惯法,有的同志认为应以目击为准,这些法律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是奴隶制法律”,如不以目击的为准,,就会把法律等同于辩证“法”、教学“法”、绘画“法”等的“法”了(见《光明日报》’1986年7月。日吴大英等文)。笔者认为,这种论点实际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已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连向梅因、摩尔根等前人的研究成果都一起否定了。事实上对任何问题如排斥逼近法、演绎法以及个体发育与系统演化相结合等等的多种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非要目击300万年以前的了、是怎样起源的,则人类起源问题将水远只能是个谜,恩格斯的从狱到人的论述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了。 (三)法学不应研究论。有的同志认为,法的“原始社会那部分(指法的起源问题)我们不可能掌握现实材料,应由历史学家去研究(见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中国法学》1987年第2期)。这就是说,法学不应该研究法的起源,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也是相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马恩选集》第3卷第155页)也正因为这样,他们高度评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把它看作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相比美。任何事物不弄清它的起源这一“基础”,不弄清它的来龙和去脉就羌法弄清它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总结出正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而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我国原始社会史的建设,对我国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法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儿乎所有的专门史,如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都必须从这里写起。弄不清人民在创造法律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以及人民维护法的公正性的斗争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树立起法律的人民主权至上观念,而坚持法的“阶级统治”观念去研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其结果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四)没有实践经验不可论证论。有的同志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意义上的法是不存在的。但我们还没有实践经验,不可能作出以具体事实为根据的科学论证”(见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中国法学》1987年第2期)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虽然没有实践经验,但却进行了规律性的预测,作了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论证,绘出了美好的大致图景,鼓舞千百万人为之而努力奋斗。恩格斯《在爱北裴特的演说》中说:“到了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争端将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马恩选集》第2卷第608页)同志也说过,“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选集》第5卷第319页)同志的论述与恩格斯的论述前后相距一百多年,具体用语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这些论断究竟有什么错误而必须抛弃不要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是不存在有任何危机的。维辛斯基法学自我封闭于“统治阶级意志”与“阶级统治”,确实存在着很大危机。随着改革、开放越深化,香港的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的实现,这种危机必将越来越大。 (五)系统的组成部分与系统整体同一论。这是惠新宋同志新近提出的“理由”。他在《评扩展了外延的法的概念及其理论意义—与苏晓阳同志商榷》一文(《政法学刊》1986年第2期)中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来看,他们认为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不存在阶级和国家。那么,原始社会没有法,共产主义社会法和国家一样要波放进历史博物馆的结论得出,恐怕不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推理。”为什么呢?在惠新宋同志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因此法律必然要与阶级、国家共始终,消灭了阶级与阶级国家,法律自然要消亡。“脱离系统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一”因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有“环保法”和“森林法”的“调整措施”,但这种“《环保法》和《森林法》不是法。”笔者认为,讨论问题不能避开历史和现实,而只从概念上去推理。历史和现实是否巳经证明了法和阶级、国家系统是同存亡、共始终的同一系统,或者法律只是阶级和国家系统的子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原始部落的社会实践与前人的科学实践,肯定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已有习惯法,习惯法也是法,它不限定在阶级和阶级国家的边界以内,这扰已经说明了问题。按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全面、系统表述,法应是社会或国家权力机关制订、认可并依其权力的强制性保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它的本质具有上述多层次的系统结构,它的基本特征:一是社会权力或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二是对社会必备行为的规范性。权力的强制性可以为剥削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所掌握(实际上是篡夺、,也可以为广大人民或人民国家所掌握,录J削阶级、阶级、阶级国家消灭了,人民或人民的国家仍存在,它不会随阶级国家的消灭而消亡。因此法和阶级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两个相互交叉的子系统,它们相互联系却又不是不可分割的,也不是以一方的存在为他方存在的前提的t’i口互依有”的. #p#分页标题#e# “脱离系统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同时“它仍具有自身的性质和功能”这一系统论原理是公认了的。惠新宋同志只要前半句,不要后半句并将之运用于说明环保法、森林法等脱离了法的体系(总体)就不再是法了。这里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而不要停留在概念推理上兜圈圈。事实上,苏联和东欧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后,把解放前的民诉法、刑诉法甚至民法中的婚姆法、继承法不予修改的承袭下来继续使用,是否这些脱离了它们原有法体系的法就不叫作法,而只能叫什么“调整措施”了呢?它失去原系统的整休性功能,却仍保存有自身的特性和功能,新政权肯定它作为一种法的特性和功能,把它放到新的系统中,又给它以新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把系统的组成部分与系统整体的特性视为完全同样,对此就是无法理解的。肯定“脱离系统整体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而又肯定“它仍具有自身的性质和功能”这才是完整的系统论原理。把“组成部分功能”完全等同于“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是违反系统论原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环保法》和《森林法》同样具有权力的强制性和对社会必备行为的规范性,具有法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只能叫作“调整措施”,而不能叫作法呢?回答只能是:因为它没有了阶级性。那么人、文学、哲学、文化、教育、艺术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都将失去阶级性,是否也都因此而不能再叫作人、文学、哲学、文化、教育、艺术,而都要苦费心机地想出什么类于“调整措施”等的’“高等动物”、“人学”、“折学”等名称来呢?一’ 三、重申几点希望 为了促进我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加强法学方法论研究,这里,笔者根据新近的情况,再次提出几点希望: (一)提高法学学术讨论水平。采用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指名点姓、注明出处的讨论,这在国外包括苏联等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我国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在学术讨论文章中指姓点名开展批评,却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搞不起来,有些批评变成了无的放矢的“客里空”,例如,有的同志先由自己主观仕撰出一个维护自己、利于自己批判的观点,然后冠上“有的人”的“客观对象”,进行“严肃”的批判。 上引的几篇文章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情况。它降低了法学理论讨论的科学水平,不利于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必将影响我国法学理论的科学化、现代化。 (二)多面向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少搞对经典著作的片面摘引,打“语录仗”。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学问题的论述具有很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在总体上又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只有全面的、系统的理解才能把握其精髓。我国法学理论上的一些问题,久争不决,与我们的学风有很大关系。在学术讨论中,对一系列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往往不敢正面接触,很多时候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一段话来作回答,而不问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人讨论的什么问题而说的。于是你引这段,我引那段,相沿成风,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我国法学理论落后,现代化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多讨论与解决实际问题,少搞些“概念搬弄”的不实之风。在社会上,现在有一股“文非”的不实之风,例如把“错误”写成“失误”,“涨价”写成“调价”等,这一不正之风也吹进了庄严的法学殿堂,例如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对于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与其他阶层的人民在法律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看待?有些论著不作如实的回答,却搬出一个“人民阶级”也是“统治阶级”i均慨念,又不对“人民阶级”概念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是基于什么情况而概括出来的?其作用和意义何在?发展前途如何等给予说明。又如,我国解放前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制订了很多法律,当时的人民政权仍不是统治阶级,国家也未正式成立,这些法是否也是法律?惠新宋同志的回答是它“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法的含义”,但“还缺少法的某些形式特征”。 至于缺少什么“形式特征”,“缺少这些形式特征”而只具实质性含义的法是否也是法?又避而不提。惠新宋同志认为“过多的限制词不是科学上严谨的表现,而是基础理论不发达,基本概念贫乏的反映。”但没有任何限制的这样搬弄、滥用概念是否沈很说明基础理论发达,基本概念就很丰富呢?笔者认为,只有按上述方向共同努力,我国法学理论界才能较快地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携起手来,面向现实,为我国法学、法治的现代化而贡献出全部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