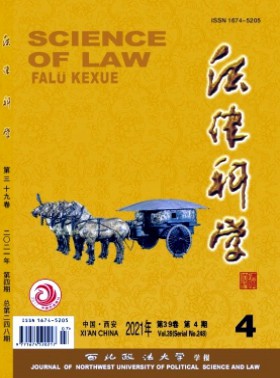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在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研究有: 1.开展了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我国是一个没有民法传统的国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不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态,而且对学术观念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的理论座谈会上,对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出现了大的争论。较为强力的观点认为民法只处理百姓之间的私的关系,例如婚姻、继承、生活借贷等,而企业之间、企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王家福先生和终柔先生等则力主民法的基本法地位。1980年王家福先生等《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民法》,伶柔先生在西南政法学院师资培训班上宣扬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商品经济,他们的观点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最终确定了民法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法地位。其直接影响,就是民法通则对民法调整对象的明确规定。 2.集中讨论了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从1980年开始,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的减税让利、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政策,学者们试图从法律的角度提供解释,提出了占有权、相对所有权、用益权、部分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法人所有权、商品所有权、企业经营权等十几种观点。此一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企业法人所有权说逐渐为大多数学者和立法所接受。对各地推行大包干合同制、企业经营自主权等,学者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法律建议。 3.学者对民事主体制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说明改革开放对民事主体制度的冲击和影响。 婚姻继承法的研究成果较多,表明学者的关注点还受制于社会生活和立法的现实。 这一阶段民法学研究的特点,一是涉及的主要是传统学科,且大多为制定某个法律的建议(重要性、必要性、主要框架等),较为宏观,对于具体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关注不够。二是学者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试图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说明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指引。三是注意引经据典,且大多以马列著作作为立论根据,引证的资料80%以上为马列著作。另外,引证较多的还有苏联民法理论,说明苏联的民法理论还占据统治地位。当然,当时客观上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了解不多,主观上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的抵制倾向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9年。此一阶段民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是: 1.对民法典的研究较为兴盛。主流学说强调民法理论和制度的普适性,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较少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特点。在物权法方面,学者开始关注所有权制度的研究,随后扩及物权法的诸多具体制度。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发表《制定物权法的基本思路》,对开展物权法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债法的研究不断深人。学者对合同法三足鼎立的批评日益高涨,并提出应当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最终使国家决定修订经济合同法,并委托学者起草统一的合同法,使我国市场经济有了统一的交易规则。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研究也开始兴起。而婚姻继承法的研究逐渐萎缩。 2.建立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张受到关注。1993年初,谢怀拭先生发表了《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经济法体系》一文。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发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考和对策建议》,使人们注意到零敲碎打式的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是不利的。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法律体系的构建,随之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几乎涉及到各种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 3.外国的法律制度和理论被大量介绍和引进,比较的方法成为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也成为最时尚的做法。从9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制度文献的使用开始大量增多,马列著作的引用则大幅减少。学术规范(至少是形式上的规范)开始受到重视。 第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本世纪初,我国统一合同法开始施行,物权法的制定紧锣密鼓地进行,民法典的制定也见诸立法机关的行动,这使得民法学研究欣欣向荣,似乎所有该研究的问题都有所涉及。而其中,围绕着法律的制定以及新法律和新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 对合同法的研究呈逐年递减的态势。学者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物权法。特别是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对“平等对待,一体保护”原则的不和谐主张导致物权法的推迟出台,社会上百姓对于物权法的强烈期待,更激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其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提上立法日程,对侵权法的研究也成为热点。 近几年,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加强。实证研究(包括社会调查和对中国法院判例的综合分析研究)的成果时有所见。随着对外交流和长期出国访问的学者的增多,对外国法律理论和制度的介绍变得较为准确和全面。法律文本的简单比较有所减少,结合外国判例进行分析和说明的文章有所增加。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国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也许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对外国的法律理论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学者充分地关注中国问题。这个阶段大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第二个阶段,是介绍、引进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并以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作为提出论点、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据。而新阶段(认真细致地研究中国特有的问题并创造出解决中国法治问题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可能刚刚开始。 总体而言,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表现就是促进和推动我国制定了主要的民事法律,民法学的体系也基本建立。但毋庸讳言,民法学也存在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我国的法学研究将不能顺畅发展。概括起来,现存的问题大致有:#p#分页标题#e# 第一,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不够,对老百姓的真正利益和法律需求了解不够。例如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权利问题,东西中部、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要求不可能相同。而不少研究者在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的框架下寻找解决方案,试图设计出统一适用的权利配置方案,这自然无法得到社会包括农民的认同。学者提出的法律草案建议稿与立法机关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在内容上出现重大差异,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学者更多地关注法律的体系性与逻辑性,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一定差距。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距离的拉大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对中国特有的问题关注不够,缺乏问题意识,尤其是缺乏中国问题意识。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及其成员对法律的需求、法律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一定与外国不同。在外国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理论上视为当然的事情,在我国现阶段却不尽然;我们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有些问题,在别的国家甚至不可能出现。对这些极具特色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升并纳人到中国的法律理论体系,本应当是学者的使命和贡献,然而,有不少学者或者忽视、或者以政治敏感性为由回避对中国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三,对法律实际运行情况关注不够,重视立法建议而缺少对法律实施机制和效果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重心是法律制定。大多数研究成果的落脚点在提出立法建议。是否提出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具体建议甚至成为评价学位论文价值的一个标准。以法律制定为中轴的研究兴趣抛物线形态也证明了这一点。学者对于法律的实施及其效果少有问津,对法律制度如何作用于社会生活关注不足,表现在研究中对法院裁判文书这一重要研究素材的忽视。近几年这种状况虽有些许改变,但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相当一批学者把研究兴趣转移到对“活的法律”的研究上来。 第四,研究方法相对贫乏,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缺少掌握。学者驾轻就熟的比较方法的使用问题最多: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而其他研究方法的欠缺,则影响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视角。 第五,学术规范方面,学风浮躁,功利主义风气弥漫,重课题轻兴趣,精品意识淡薄。现有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以及命题作文式的课题(项目)制,在客观上无疑起着不良的引导作用,但学者的学术心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引注方面,失范现象较为常见:一是为引注而引注。一篇文章引注几十上百个,其中有许多大部头的外文书,作者是否都仔细读过,值得怀疑。二是大段援引外国人的观点,并以其作为文章说理逻辑的大前提。三是有选择地引用,只引和自己的主张相同的观点。四是喜欢引用外国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语录,法学家的观点则较少引用。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现在甚至出现了伪造引注的现象。另外,学者间的学术争论没有充分开展,难以形成学术焦点,研究的深度受到影响。 故此,我以为我国的法学研究现在面临着转型问题。当着我们对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有了较为准确和全面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当着外国的制度和理论在用来解决中国的某些实际问题时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的时候,再简单套用外国的制度和理论来为中国法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就学术发展和学术贡献而言,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当别人的学生。如果说外国的法律学术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可以被我们所继承,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些让外国人继承的法律文化遗产呢?上世纪末,在《法学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不要追求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或者说不必刻意追求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有学者认为法学太过强调为社会实践服务,会忽视学术本身的问题,认为如果一切研究都首先考虑能否被人民和政治家接受,就会使研究偏离学术性。这些说法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法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首先应该用于、而且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社会有其自己的体系,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法律理论的体系和逻辑应当尽量靠近社会生活的体系和逻辑,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体系应当借鉴但不一定要因循。也许,在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时提出的理论和设计的制度相互之间有着体系上的若干不协调(其实并非不可避免),在制度理论和制度建构较为丰富和完备时,我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原则和精神的统领下,从体系和逻辑上尽可能将其理顺。不可以认为外国人为我们提供的是完美和唯一正确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逻辑体系,否则我们的任务就可以简化成为翻译、介绍、注释和内容填空。 我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的转型,简而言之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单纯的理论构建转向宏观法治对策研究(非微观对策)。2.从单纯的案头研究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3.从立法研究更多地转向解释论研究。4.从对法律制度的逻辑批评转向效果评判。5.从封闭的、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转向讨论和争鸣,进行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 当然,目前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也应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