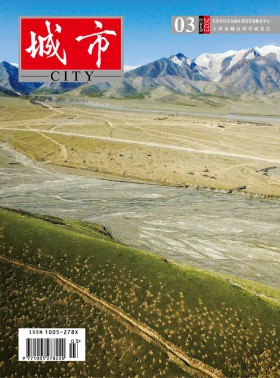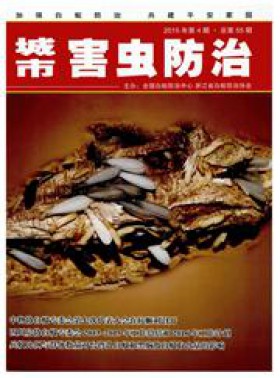作者:顾书桂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住房群租(以下简称群租)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2006年上海就开始打击群租,2011年打击群租更上升成为中国国家层面的行政行为。单纯从打击群租的范围由上海扩大到全国看,不难断言21世纪前10年群租在中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群租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的常态选择。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群租产生的原因,从而为中国群租问题的根治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群租的定义与危害性
住房群租是一个新名词,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基本内涵比较容易把握。根据上海市《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居住房屋应当以原规划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分门进出的客厅、厨房、卫生间等均不得单独出租;一间房屋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出租给家庭的,家庭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居住房屋不得分割搭建若干小间,按间或按床位出(转)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从上海与国家的两个版本的规定看,群租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低于最低标准;第二,缺乏独立的进出通道;第三,出租房间小于原规划设计。其中,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低于最低标准是群租最核心的内容,因为人均租住建筑面积过低是缺乏进出通道和原规划设计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以人均租住建筑面积过低为特征的群租最明显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承租人房租较低,二是出租人租金极大化。但群租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承租人来说,群租的家具设施十分简陋,卫生条件差,房东只收钱不管理,居住环境比较恶劣;对邻居和居住小区其他业主来说,群租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因为单位建筑面积的居住者数量过多,会导致建筑物负载加大,物业设施设备负荷增加,不仅带来消防隐患,相邻业主的居住环境也会变差;特别是群租人员杂,流动性大,不仅可能扰民,更会带来治安问题。然而在危害如此之多、之大的前提下,群租在中国愈演愈烈,只能说明群租在现阶段的中国有明显的合理性。那种片面强调取缔群租的行为,对自住业主而言是狭隘的极端利己主义,对政府而言则是治标不治本的敷衍塞责。中国的群租现象远没有人们现在所想的那么简单。
二、土地财政是中国群租愈演愈烈的根源
理论上来说,群租首先应该与住宅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有关。从城市住宅供求的基本原理(顾书桂,2010年)看,城市住宅供给分两种,即优质住宅和普通住宅;优质住宅供给刚性,提供效用的绝对额大,必须遵循市场竞购原则,因此与普通消费者的关系不大;普通住宅由于地基供给限制条件相对较少,供给弹性较强,从而可以满足所有消费者的基本居住需求。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住宅只是可以满足所有消费者的基本居住需求,而不是没有任何限制。这是因为:第一,普通住宅也有生产成本,低于这一成本的市场价格,是不可能激励厂商将普通住宅提供出来的;第二,普通住宅的建安材料可以由市场竞争性供给,但地基有可能因为政府垄断而使供给刚性,因此普通住宅的供给弹性是以普通住宅地基的供给弹性为前提的;第三,市场机制内在地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因此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第四,住宅作为最大宗的基本消费资料,当其作为商品时,购买力不足的消费者群体规模是最大的。这四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完全依靠市场,消费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能满足自己的基本居住需求的。所有消费者都能满足自己的基本居住需求的可能性与政府充分履行公共财政职能特别是住房保障职能密切相关。市场比政府更能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只能推导出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不能下结论说市场能够完全取代政府的作用。相反,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在市场失灵的局部领域,政府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住房保障就是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对相关消费者而言就是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这种提高是相对的,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从而增强他们在普通住宅市场的购买力,使他们由原来的买不起变为现在的买得起,也可以直接降低普通住宅的支付价格,间接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一样能够实现他们住有所居的最终目标。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具体模式选择,既取决于政府的主观决策和客观财力,更取决于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住房保障有一个最佳规模。它涵盖不能足额支付商品化普通住宅生产价格的所有中低收入消费者,因为政府提供住房保障必须依靠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税率不变的时候,税基越大,征税额越大,反之则越小。由于面向普通住宅的消费者的基本居住需求是刚性的,而面向优质住宅的消费者的发展和享受居住需求是弹性的。这就是说,政府保障的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在住房保障需求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政府从优质住宅消费者那里获取的财政收入因为优质住宅消费者规模的急剧收缩而会迅速变少,因而保障能力大大变小。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财政收支矛盾会迫使政府将住房保障规模限制在最优的均衡点上。当然,如果政府没有住房保障的压力,不仅意味着市场均衡点以下的中低收入消费者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还意味着普通住宅的生产价格不再稳定,而会像优质住宅一样螺旋式上升,甚至比优质住宅上升得更快(顾书桂,2011年)。原因在于当代社会,政府不是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就是垄断了土地开发权(张俊,2007年)。作为商品的土地的市场价格越高,政府从中获得的财产税、流转税、所得税和行为税等就越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角度出发,政府也有推高地价从而推高房价的强大动力。当普通住宅市场价格由于政府推动而离开均衡点变得越来越高时,支付能力不足的消费者规模当然也就越来越大。对这部分消费者来说,基本的居住需求不能通过市场购买或政府保障得到正常满足,就只能通过群租的方式非正常地得到满足;对政府来说,由于摆脱了住房保障的制约,政府利用自身的行政垄断权力或垄断的土地所有权肆意推高房价而追求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无疑是土地财政的最典型形式。中国自1998年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以上海为代表,群租愈演愈烈,除了用土地财政来解释外,很难找出其他理由。#p#分页标题#e#
三、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是群租的主要恶果
群租无疑会影响群租者本身及其邻居的生活质量,但这些都属于表象层面和枝节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才是群租的主要恶果。群租首先影响城市移民的劳动力再生产。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城市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汇合着最先进的生产要素,从机器大工业到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着城市经济不断前行。在城市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不仅决定着单个生产要素的质和量,还决定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可能比单个生产要素的质和量更重要。如果说国际间竞争虽然也包括资源和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和体制的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体制、资源和技术的差异相对消失,城市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简化为人才的竞争,争取质优价廉的移民恰恰是城市人才竞争的重要内容。移民对一个城市而言,不仅代表着新产品和新技术,还可能代表着新观念和新思维,从而有利于在有形创新和无形创新两个方面推动城市站上国内以致国际竞争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制高点。然而由于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这种缺陷可能来自市场发育不够,也可能来自市场高度发育),移民的劳动力价值有可能在市场上得不到充分兑现,或得到充分兑现的时间太短。总之,尽管移民的技术和观念对他们所在的城市很重要,但他们的工资不足以满足劳动力更新的最低需要,他们依然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特别是住房保障。群租不仅意味着移民没有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最低需要的住房保障,还意味着他们又被土地财政盘剥了一次。因为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缺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孪生的,土地财政引发的高房价同样最终会体现在城市住房的高租金上。由于群租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居住标准,城市移民只能以萎缩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城市移民的增量越来越少,即使城市移民的存量规模不缩减,其素质也会大大下降。除了移民以外,群租对城市原有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也会产生不利影响。短期看,相当一部分城市原有居民会成为群租的受益者,因为他们不但住有所居,而且还可能有闲置房;他们不但不会受到群租的盘剥,相反他们还可以利用闲置房源进行群租来盘剥移民。然而从长期看,这种受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土地财政会让所有的普通住宅像优质住宅一样被竞购,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结果只会使社会房源越来越集中,有闲置房源的城市居民比重会越来越小,在某一个临界点上,城市原有居民终究会取代移民成为群租的主要客源,则群租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利影响同样会落到城市原有居民身上,从而阻碍城市原有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临界点,群租也可以通过恶化国民经济的发展环境而阻碍劳动力的顺利再生产,因为群租意味着高房价,意味着居民的过度储蓄,意味着居民的正常消费被压制;也意味着政府没有弥补市场缺陷,没有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没有提供市场机制良性运行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还意味着土地所有者榨取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土地投机盛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被扭曲。群租不仅导致国民经济畸形运转,更有可能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再生产的外在环境遭到破坏,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在动力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群租不仅是一个移民问题,也是一个最终涉及所有人的民生问题。群租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其可能带来的却是一个重大问题,即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为了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群租问题必须加以解决。然而从目前来看,中国常见的头痛砍头式的片面取缔,不但无助于群租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直接危及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片面取缔群租是徒劳之举
群租出现的原因是: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缺失,土地财政将普通住宅价格推得过高,从而使得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难以支付最低限度的居住成本。因此取缔群租的根本措施在于,将过高的普通住宅价格降低到相对稳定的生产价格水平,对基本具备市场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财政援助,以满足其对商品化住宅的居住需求,对基本不具备市场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则应由政府通过取消住宅商品化属性的方法使消费者居住的需求价格与公共住宅的供给价格实现衔接。然而从中国取缔住房群租与中国降低房价、建设保障房的时间冲突看,中国治理群租的方式是典型的头痛砍头式的片面取缔。因为中国打击群租行为的时间很早,上海是2006年,全国是2011年。然而中国住房群租现象泛滥的大中城市商品房价停涨是2011年12月到2012年1月,商品房价何时下降则无法预测[1]。中国保障房建设更是漏洞百出(顾书桂,2012年),“十二五”期间全国计划兴建3600万套保障房,前两年每年安排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鉴于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落实问题过于严重[2],2012年被迫调整为700万套,即使这样,资金问题依然是拦路虎[3]。本质上看,在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职能的前提下,片面取缔群租,不但不能根治群租问题,反而会使群租问题恶化。
第一,片面取缔群租不可能改变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居住需求是刚性的基本需求,消费者牺牲居住的最低标准选择群租本身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在不提高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支付能力的情况下,片面取缔群租不会使中低收入人群转向基本合乎需要的住房。住宅市场不是慈善机构,居住环境的改善是以居住成本的提高为代价的,低收入的消费者无力支付更高的成本,当然就无法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所以摆脱群租的生活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第二,片面取缔群租不可能使房地产投资者得利。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买不起可以租。实际情况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如果买不起住房,就更租不起住房,因为理论上商业租赁价格就应该高于市场购买价格[4]。片面取缔群租当然不可能改善消费者的居住环境,即使假定能够改善,它对房地产投资者的利益也是一种伤害,因为同样的闲置房源,如果入住者减少,房屋租金的总量也相应减少了。群租固然对消费者是一种伤害,但对房东却是利益最大化的一条途径,它会榨干中低收入消费者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铜板。
第三,片面取缔群租会间接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片面取缔群租的后果,是群租以更偷偷摸摸的形式进行,或是中低收入消费者特别是移民远离这座城市。处于非法状态的群租对中低收入消费者而言更是一场灾难,因为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应有权益更加得不到保障。中低收入消费者远离这座城市,不仅意味着以城市移民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流动的失败,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经济效率的损失和这座城市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在经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后最终也会上升。最典型的是,每逢春节期间,由于大批农民工返乡,中国大中城市的一般用工成本都会大幅度地上升。所以那种认为强制城市移民增加住房消费有利于刺激当地住房租赁市场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p#分页标题#e#
第四,片面取缔群租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二元经济国家,过剩劳动力还没有完全从广大的农村转移出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农业现代化改造的难度越大,中国越难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现代化。中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最大限度吸收,离不开城市对农民离开农村土地的支持。片面取缔群租,将把农民从城市赶回农村,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五、大中城市的保障房建设是解决群租问题的关键
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普通住宅价格急剧上涨,中国的住房保障问题已经激化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与此同时,城市的集聚效应越明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越强,普通住宅价格越偏离均衡水平,因此中国的群租问题实际上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的,即城市规模越大,群租问题越严重。因此,大中城市的保障房建设成了解决群租问题的关键。然而从目前来看,大中城市的保障房建设不容乐观。
首先,保障房建设受到住宅投资者的反对。在理论上,住宅投资的对象都是优质住宅,普通住宅因为供给富有弹性,增值潜力有限而且风险大,通常被放弃。然而在中国,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缺失,土地财政将普通住宅也变成了住宅投资对象,甚至变成中国住宅投资的主要对象(顾书桂,2011年)。普通住宅价格依靠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的垄断,不仅可以有稳定的预期,而且可以稳步上涨,这种政策收益比投资优质住宅的有风险的市场收益诱惑大得多,中国因此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炒房市场。保障房特别是大中城市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势必将原已炒得过高的普通商品房价打压下来,从而使得那些普通住宅的市场投资者丧失收益兑现的机会。在中国,普通住宅的供应规模远远大于优质住宅的供应规模,相应地,普通住宅投资者的规模也远远大于优质住宅投资者的规模,普通住宅投资者的激烈反对是中国大中城市保障房建设的重大阻力之一。
其次,保障房建设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对。群租直接起因于城市高房价,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乏住房保障制度约束的土地财政。作为土地财政的主要受益者,地方政府当然构成保障房建设的最主要反对力量(顾书桂,2010年)。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反对,既与土地出让收入可能流失有关,更与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大幅度下挫有关。因为保障房建设不会允许地方政府以市场价格拍卖住宅建设用地,曾经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会一去不返;保障房建设必然会冲击现有的普通住宅投资,普通住宅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势必带动普通住宅价格的下行,从而使普通住宅的土地出让价格也大幅度下挫,这又会让地方政府手中的住宅储备用地贬值。鉴于地方政府是保障房建设的主体,保障房建设对其自身利益的损害足以使它们即使不公开反对保障房建设,也会在暗中消极怠工甚至破坏全国保障房建设的整体规划。
再次,保障房建设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反对。在住宅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住宅用地价格的高低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平均利润其实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没有大的影响。因此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重要的是住房建设本身,至于住房是商品性质的还是保障性质的,并不重要。然而在过去十多年中,由于土地财政的支配,中国住宅市场始终处于失衡状态。伴随着住宅市场价格的一路猛涨,中国住宅用地价格也一路飙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不仅获得了房产开发的平均利润,更获得了地价上涨的巨额收益,中国房地产领域成为过去几年中国富豪最集中的诞生地。保障房建设虽然不会妨碍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平均利润,但房地产开发商会因为地价上涨收益可能的损失而下意识地反对保障房建设(顾书桂,2012年)。
最后,保障房建设甚至受到普通城市居民的反对。理论上,普通城市居民虽然也拥有商品化住宅的所有权,但他们更关心住宅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住宅的价值,因此与普通住宅投资者相比,他们应该能够比较宽容地对待甚至欢迎保障性住宅的建设。然而土地财政推高的房价挤占了城市普通居民其他正常的消费乃至一些刚性的需求(如养老、教育、医疗等),消费者满足这些刚性需求的支付能力不得不暂时以商品化住房的形式存在着。商品化住房的价格上升,意味着城市普通居民满足自身刚性需求的支付能力更有保证,反之则反是。保障房建设对普通住宅市场价格未来的冲击是确定无疑的,这可能是普通城市居民反对保障房建设的最主要理由。
从中国保障房建设可能遇到的四种阻力来看,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难化解的。因为将普通住宅作为主要投资对象的中国住宅投资者,一开始玩的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从他们的投资行为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破灭,惟一不能确定的是,价格泡沫破灭的损失将具体由哪些人承担。对于这种零和游戏的市场博弈行为,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为他们买单。房地产开发商对保障房建设的反对源于非常态的地价上升收益,但保障房建设并没有损害房地产开发商获取平均利润的环境和条件,这本身就注定了房地产开发商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反对具有不彻底性,特别是随着住宅市场供求趋于均衡,房地产开发商对保障房建设的暂时反对更有可能转变为对保障房建设的积极参与。城市普通居民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反对要区别对待,一部分居民拥有较多的商品房,其实已经与普通住宅投资者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可能的损失应该由市场买单;一部分居民只有自住的房源,而且基本上在刚性需求的范围内,但这有限的住房同样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下跌会危害到其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义务弥补他们的损失。这样,城市普通居民对保障性住宅建设的反对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地方政府固守土地财政对保障房建设的反对只能依靠制度化解。没有刚性的制度安排,单纯依靠行政压力或者道德说教,地方政府即使支持保障房建设也是暂时的,而对保障房建设的反对则是持久的。刚性的制度安排必须确保政府利用土地垄断权推高普通住宅市场价格得不偿失,从而将普通住宅市场的价格和规模控制在最佳的水平上。在这一水平上,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规模是最小的,成本是最低的,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动。总之,群租问题的根子在土地财政,解决群租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